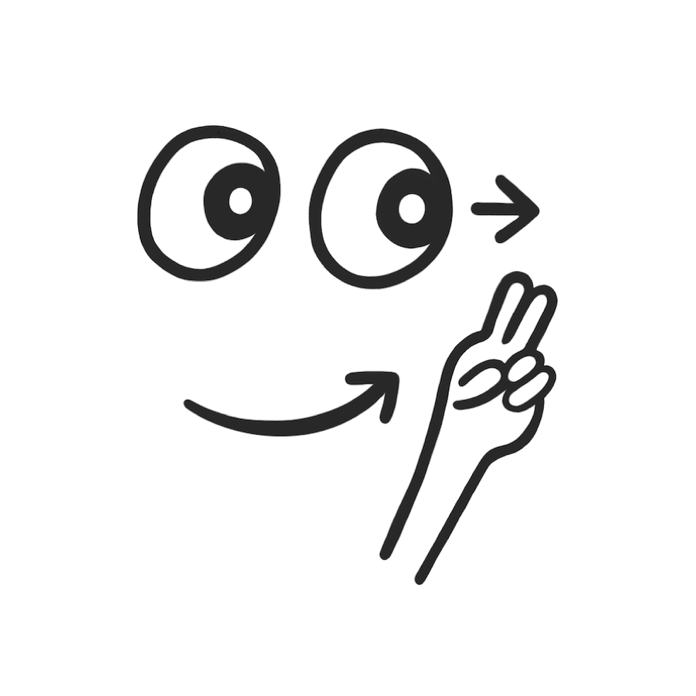解析《維摩詰所說經》
《維摩詰所說經》,又稱《維摩詰經》。主角維摩詰,以居士身份來教化大眾。維摩詰臥病在床,釋迦牟尼讓他的弟子去探病,但是因為某些原因表達自己不敢去的原因,以及對他的敬畏。
【入諸婬舍,示欲之過;入諸酒肆,能立其志。】《方便品第二》
維摩詰走入妓院,藉機向眾人說明縱欲帶來的禍患;走入鬧市酒館,勵志勸人。
經文中以維摩詰的病來告訴一切皆無常,身體無知如草木瓦礫,不淨穢惡,充滿苦痛,會朽壞,不過是顛倒夢想的錯覺,一個聚合體罷了,本質上是「空」。法常寂然、無名字、無言喻、無我、無分別、無相、無高下、無美醜、常住不動。
在這篇解析中,會探討經文中有道理的地方,但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觀念參雜在裡面。
罪業並非真實存在
【憶念昔者,有二比丘犯律行,以為恥不敢問佛,來問我言:『唯,優波離!我等犯律,誠以為恥,不敢問佛,願解疑悔,得免斯咎。』我即為其如法解說。時維摩詰來謂我言:『唯,優波離!無重增此二比丘罪!當直除滅,勿擾其心。所以者何?彼罪性不在內、不在外、不在中間,如佛所說,心垢故眾生垢,心淨故眾生淨。心亦不在內、不在外、不在中間,如其心然,罪垢亦然,諸法亦然,不出於如如。優波離!以心相得解脫時,寧有垢不?』我言:『不也!』維摩詰言:『一切眾生心相無垢,亦復如是。唯,優波離!妄想是垢,無妄想是淨;顛倒是垢,無顛倒是淨;取我是垢,不取我是淨。優波離!一切法生滅不住,如幻如電,諸法不相待,乃至一念不住;諸法皆妄見,如夢、如炎、如水中月、如鏡中像,以妄想生。其知此者,是名奉律;其知此者,是名善解。』】《弟子品第三》
優波離說:「我記得以前曾經有兩個比丘犯了戒,感到羞愧,不敢直接問釋迦牟尼,就來問我:『優波離,我們犯了戒律,感到羞愧,不敢問佛陀,希望您能為我們解答疑惑,消除悔恨,讓我們免於罪過。』我便按照戒律為他們作了解說。」
這時,維摩詰居士過來對我說:『優波離!不要加重這兩位比丘的罪過!應當直接消除他們的罪業,而不是讓他們心裡更不安。為什麼呢?因為罪性的本質不在內、不在外、也不在中間。正如佛陀所說:心垢,眾生就垢;心淨,眾生就淨。心也不在內、不在外、不在中間。就像心一樣,罪垢也是如此,一切法也是如此,都不出於如如實相。
「優波離!當心相得到解脫時,還會有垢染嗎?」我回答:「不會!」維摩詰居士接著說:「一切眾生的心相本來無垢,也是如此。優波離!妄想是垢染,沒有妄想就是清淨;顛倒執著是垢染,沒有顛倒執著就是清淨;執著自我是垢染,不執著自我就是清淨。優波離!一切法都是生滅無常的,像幻影、閃電一樣,諸法並不相互依存,甚至連一念都無法停留;一切法都是虛妄的顯現,如同夢境、幻影、水中月、鏡中像,都是因為妄想而生。明白這個道理的人,才是真正持戒;明白這個道理的人,才是真正善解佛法。」
註解:
這段說得很好。罪業和清淨的本質都是心念的顯現,心念的本質是空性,罪業並非實有。所以只要明白,不再有這些錯誤的認定或想法,罪業也就自然就消除了。
【不斷婬、怒、癡,亦不與俱;不壞於身,而隨一相;不滅癡愛,起於明脫;以五逆相而得解脫,亦不解不縛;不見四諦,非不見諦;非得果,非不得果;非凡夫,非離凡夫法;非聖人,非不聖人;雖成就一切法,而離諸法相,乃可取食。若須菩提不見佛,不聞法,彼外道六師——富蘭那迦葉、末伽梨拘賒梨子、刪闍夜毘羅胝子、阿耆多翅舍欽婆羅、迦羅鳩馱迦旃延、尼犍陀若提子等——是汝之師,因其出家,彼師所墮,汝亦隨墮,乃可取食。若須菩提入諸邪見,不到彼岸;住於八難,不得無難;同於煩惱,離清淨法;汝得無諍三昧,一切眾生亦得是定——其施汝者,不名福田;供養汝者,墮三惡道——為與眾魔共一手作諸勞侶——汝與眾魔及諸塵勞,等無有異——於一切眾生而有怨心,謗諸佛,毀於法,不入眾數,終不得滅度。汝若如是,乃可取食。』】《弟子品第三》
不用完全斷絕欲望(婬)、憤怒(怒)和無明(癡),但也不被這些情緒所束縛;不執著於身體的實有,也不否定身體的存在;不刻意消滅無明(癡)和貪愛,而是通過智慧(明)達到解脫;看似犯下極大罪過(譬如五逆重罪),但不落於“束縛”或“解脫”,所以能從中解脫;也不執著四聖諦的教法,但也不是完全無視;不執著於是否證得果位,修行成就,但也不是沒有成就;超越了凡夫的境界,但也不完全脫離凡夫的狀態;具有聖人的智慧,但也不自認為是聖人;成就一切修行法門,但不執著於任何法相,不執著於某種現象或概念……只有這樣才可拿這飯。
如果你須菩提不見佛、不聞法,甚至把外道六師都視為你的老師,並跟他們一起出家、一起墮落,那時候你才能拿飯。
註解:
這種解釋有些模糊, 在某種意義上說的沒有錯,但是另一個層面也不完全正確。正確的部分是,明白了幻相現實的運作,不困在某一個認定裡,而自在解脫。但也可能沒有真正見性,只是頭腦概念層面,以為善惡不分別;沒有解決自己情緒的問題,只是假裝看過去,說情緒只是幻相的一部分; 沒有直面自己的貪瞋痴、無名,卻說那些都是空相。那麼則會落入瑪雅的陷阱。
靜坐,不是靜靜坐著不動
【舍利弗白佛言:「世尊!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?憶念我昔,曾於林中宴坐樹下,時維摩詰來謂我言:『唯,舍利弗!不必是坐,為宴坐也。夫宴坐者,不於三界現身、意,是為宴坐;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,是為宴坐;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,是為宴坐;心不住內亦不在外,是為宴坐;於諸見不動,而修行三十七品,是為宴坐;不斷煩惱而入涅槃,是為宴坐。若能如是坐者,佛所印可。』】
我在樹林中靜坐修行,維摩詰居士來到我面前,對我說:「舍利弗!真正的靜坐,並不是像你這樣坐在樹下才叫靜坐。真正的靜坐,是不在三界(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)中顯現身心,這才是靜坐;不離開滅盡定(一種深層禪定),卻能展現各種威儀行為,這才是靜坐;不捨棄佛法,卻能行凡夫之事,這才是靜坐;心不執著於內,也不執著於外,這才是靜坐;在各種見解中不動搖,卻能修行三十七道品,這才是靜坐;不斷除煩惱卻能進入涅槃,這才是靜坐。如果能這樣靜坐,才是佛陀所認可的。」
註解:
在這裡,維摩詰這句「不必是坐,為宴坐也。」說得沒錯,宴坐不在坐。靜坐冥想,不是靜靜坐著不動,不做判斷的看著想法來,又看著想法去。但其他部分就比較難說完全正確了。
所以《維摩詰經》中大概就是上面提到的兩個話題,關於罪業和靜坐,是正確的以外。 其他的觀念不能說完全全錯,但似是而非,很多屬於頑空。
頑空,困在空相
【唯,大目連!為白衣居士說法,不當如仁者所說。夫說法者,當如法說。法無眾生,離眾生垢故;法無有我,離我垢故;法無壽命,離生死故;法無有人,前後際斷故;法常寂然,滅諸相故;法離於相,無所緣故;法無名字,言語斷故;法無有說,離覺觀故;法無形相,如虛空故;法無戲論,畢竟空故;法無我所,離我所故;法無分別,離諸識故;法無有比,無相待故;法不屬因,不在緣故;法同法性,入諸法故;法隨於如,無所隨故;法住實際,諸邊不動故;法無動搖,不依六塵故;法無去來,常不住故;法順空,隨無相,應無作;法離好醜,法無增損,法無生滅,法無所歸;法過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心;法無高下,法常住不動,法離一切觀行。唯,大目連!法相如是,豈可說乎?夫說法者,無說無示;其聽法者,無聞無得,譬如幻士,為幻人說法,當建是意,而為說法。當了眾生根有利鈍,善於知見無所罣礙,以大悲心讚于大乘,念報佛恩不斷三寶,然後說法。』】
佛法本來沒有“眾生”的概念,因為它遠離了眾生的污垢;也沒有“我”的概念,因為它超脫了自我之污;沒有壽命,脫離了生死;沒有“有人”的概念,前後皆斷;
本來就常寂靜,所有形相都會消失;脫離了形相,便無所依據;沒有固定名字,因為言語也無法完全表達;也無需言說,因為超越了覺觀;沒有固定形狀,猶如虛空;
沒有爭辯、戲論,終究是一切空相;也不執著於“我所擁有”,超越了一切分別;更無可比較,也無相待;不依因,不在緣;與法性合一,貫通一切;雖然隨真如而行,卻無所依附;
安住在究竟實相,四周不動;不受六塵牽制,也不會動搖;無去無來,恆常不變;順應空性,隨無形相而作,無為而生;
超越好醜,無增無減,無生無滅,無所依歸;甚至超越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心;既無高下,又恆常不動,並超越了一切分別。
【以空聚想,入於聚落,所見色與盲等,所聞聲與響等,所嗅香與風等,所食味不分別,受諸觸如智證,知諸法如幻相,無自性,無他性,本自不然,今則無滅。】
把自己看作『空空的器皿』,不帶任何執著或分別心地進城乞食;見到了色相,就像盲人看不見;聽到了聲音,就像回聲一般;聞到了香味,當作吹過的風;吃到了味道,不做分別;感受到的一切觸覺,如同智慧所證的空境。明白一切現象皆是幻相,沒有『我』的本性,也沒有外在『他物』的本性,本來就沒有生起,現在也沒有滅去。
註解:
「空空的器皿」這種解釋是典型的「斷滅空」、「頑空」,對於「空」的執取、斷見,把所有一切都視為幻相,這種「空」並不是真正的「空」,困在空相的概念中。
如果見到了色相,就像盲人看不見,聽到了聲音,就像回聲一般;聞到了香味,當作吹過的風;食之無味。這種練習會造成感官覺知上的抽離,導致自己對周遭事物變得不敏感。
這類似《六祖壇經.頓漸品》,六祖批評神會的例子:
惠能大師用拄杖打了神會三下,問:「我打你,你痛不痛?」
神會回答:「也痛也不痛。」
惠能大師說:「我也見也不見。」
神會問:「什麼是『也見也不見』?」
惠能大師說:「我所見的,是常常反省自己,不見他人的是非好惡,所以說是『也見,也不見』。你說『也痛,也不痛』是什麼意思?如果你不痛,就和木石一樣;如果你痛,就和凡夫一樣,會生起怨恨。你剛才問的『見、不見』是二元分別,但『痛、不痛』是生滅的分別。你連自己的自性都沒見到,還敢來戲弄人!」
混淆二元
【善、不善為二。若不起善、不善,入無相際而通達者,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】《不二法門品第九》
善與不善是二。如果不生起善與不善的念頭,進入無相境界而通達,這就是入不二法門。
【生死、涅槃為二。若見生死性,則無生死,無縛無解,不然不滅,如是解者,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】
生死與涅槃是二。如果見到生死性,就沒有生死,無縛無解,不生不滅,這樣理解,就是入不二法門。
註解:
認為「不二法門」是「超越」一切對立、分別的境界,但如果繼續剖析什麼是「超越」?怎麼超越?會發現那些只是頭腦想像出來的「超越」、「不分別」、「智慧」,一些無法應用在現實中的假設。一大堆形而上的「空」話,一堆似是而非的二元「哲理」,繞來繞去,對於解決現實問題沒有幫助。
如果一個人夠誠實,聆聽自己的內心感受和想法,就會發現那些只是一些沒有用的理論,因為發現內心情緒過不去,現實問題解決不了。現實生活中,不可能沒有差別,不可能不明辨是非,把全部東西含糊一團,說服自己一切都是假象。
別亂說話!佛怎麼可能生病?
【阿難白佛言:「世尊!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?憶念昔時,世尊身小有疾,當用牛乳,我即持鉢,詣大婆羅門家門下立。時維摩詰來謂我言:『唯,阿難!何為晨朝持鉢住此?』我言:『居士!世尊身小有疾,當用牛乳,故來至此。』維摩詰言:『止,止!阿難!莫作是語!如來身者,金剛之體,諸惡已斷,眾善普會,當有何疾?當有何惱?默往!阿難!勿謗如來,莫使異人聞此麁言;無令大威德諸天,及他方淨土諸來菩薩得聞斯語。阿難!轉輪聖王以少福故,尚得無病,豈況如來無量福會普勝者哉?行矣,阿難!勿使我等受斯恥也。外道、梵志若聞此語,當作是念:「何名為師?自疾不能救,而能救諸疾人?」可密速去,勿使人聞。當知——阿難!——諸如來身,即是法身,非思欲身。佛為世尊,過於三界;佛身無漏,諸漏已盡;佛身無為,不墮諸數。如此之身,當有何疾?當有何惱?』時我——世尊!——實懷慚愧,得無近佛而謬聽耶?即聞空中聲曰:『阿難!如居士言。但為佛出五濁惡世,現行斯法,度脫眾生。行矣,阿難!取乳勿慚。』世尊!維摩詰智慧辯才,為若此也!是故不任詣彼問疾。」】《弟子品第三》
世尊有小病,所以當時我拿著鉢子,到一位大婆羅門家門下托缽牛乳來給你治病。維摩詰走過來問我:『阿難啊,為什麼一大早拿著鉢子站在這裡?』我說:『因為居士,世尊身上有點小病,所以用牛乳治療。』維摩詰說:『住口,住口,阿難!別這樣說!如來的身體,猶如金剛般堅固,早已斷除了所有惡習,聚集了無數善德,怎麼可能有病?生煩惱?快走吧,阿難!不要毀謗如來,別讓人聽到這粗俗的話。不要讓大威德的天神和其他淨土的菩薩聽到了。阿難啊,即便是少福報的轉輪聖王都不會得病,何況是福德無量無邊的如來。走吧,阿難!別讓我們受這種恥辱。
註解:
一個人成就不成就,都可能生病,所以佛也會生病。畢竟身體就是一台生物機器,就像任何機器一樣,都有可能故障,跟福德、業力沒有任何關係。
我病了,因為眾生病了
【維摩詰言:「從癡、有愛,則我病生。以一切眾生病,是故我病;若一切眾生病滅,則我病滅。所以者何?菩薩為眾生故入生死,有生死則有病;若眾生得離病者,則菩薩無復病。譬如長者唯有一子。其子得病,父母亦病;若子病愈,父母亦愈。菩薩如是,於諸眾生愛之若子。眾生病,則菩薩病;眾生病愈,菩薩亦愈。又言『是疾何所因起?』菩薩病者,以大悲起。」】《問疾品第五》
從癡迷而生貪愛,我的病因此而生。因為一切眾生病了,所以我病了;若一切眾生病消失了,則我的病也就痊癒了。為什麼?菩薩為了度眾生而入生死,有生死則有病;若眾生遠離病痛,則菩薩也不再有病。好比孩子得病了,父母擔憂,所以也得病;若孩子痊癒了,父母也就痊癒了。對菩薩來說,一切眾生就像自己的孩子;只要眾生有病,菩薩就像父母一樣,也會‘生病’,而眾生病好了,菩薩的病也就痊癒了。如果你問:『菩薩這種病是怎麼來的?』菩薩之所以生病,其實是源自他對眾生的大慈悲心。
註解:
別把大悲作為推托。如果有人說菩薩救助眾生要背因果,只能說那人不是真菩薩,自己能力不足,卻把自己的生病推給別人。成就者不會背業,並不是說成就者不會生病,生活中不會碰到糟心事,但那些事情跟眾生無關。
一切皆空空,我的病無形,不可見
【文殊師利言:「居士!此室何以空無侍者?」維摩詰言:「諸佛國土亦復皆空。」又問:「以何為空?」答曰:「以空空。」又問:「空何用空?」答曰:「以無分別空故空。」又問:「空可分別耶?」答曰:「分別亦空。」又問:「空當於何求?」答曰:「當於六十二見中求。」又問:「六十二見當於何求?」答曰:「當於諸佛解脫中求。」又問:「諸佛解脫當於何求?」答曰:「當於一切眾生心行中求。又仁所問:『何無侍者?』一切眾魔及諸外道,皆吾侍也。所以者何?眾魔者樂生死,菩薩於生死而不捨;外道者樂諸見,菩薩於諸見而不動。」】
文殊師利問:「居士!這個房間裡為什麼沒有侍者?」維摩詰回答:「因為就連各佛的國土也是空的。」
再問:「那空又是根據什麼而空呢?」維摩詰答道:「以空空。」
接著問:「空這個概念,存在的目的或用處是什麼呢?」答道:「因為無分別而空,所以才是空。」
問:「那空本身可以再做分別嗎?」答:「分別本身也空。」
再問:「那我們應該到哪裡去尋求這個空呢?」答道:「應該在六十二見中去尋求。」
追問:「那這六十二見又應該到哪裡去求呢?」回答:「應該在諸佛解脫中去求。」
繼續問:「那諸佛的解脫又應該到哪裡去求呢?」答:「應該在一切眾生心行中求。」
又追問:「那為什麼說這裡沒有侍者呢?」回答:「一切眾魔和外道都是我的侍從。」無明、貪嗔痴等“眾魔”沉迷於生死輪迴,菩薩雖然身處生死輪迴中,但不執著於生死;外道執著於種種見解認定,但菩薩不被種種見解認定所左右。
【文殊師利言:「居士所疾為何等相?」維摩詰言:「我病無形不可見。」】
文殊師利問:「居士,你的病有什麼症狀?」維摩詰答:「我的病無形,不可見。」
【今我此病,皆從前世妄想顛倒、諸煩惱生,無有實法,誰受病者?所以者何?四大合故,假名為身;四大無主,身亦無我。又此病起,皆由著我,是故於我不應生著⋯⋯】《問疾品第五》
現在我生病,都是由我前世的顛倒、妄想、煩惱所生,這些都是虛妄、不真實的。是誰在承受這病呢?所謂的「身」,只不過是四大(地水火風)暫時聚合而成的一個假名;而四大本身沒有主,所以「身」也沒有固定的我。這病之所以生起,是因為對「我」產生了執著,所以不應該執著有個「我」在受病。
註解:
如果我是禪師,可能會給他一記當頭棒喝,不要頭腦這麼雜亂,停不下來。表面上聽起來很有道理,但其實在形而上的概念繞來繞去,似是而非的觀點,解釋繁冗,缺乏解決問題的針對性,繞得大家暈頭轉向。誠實地問自己,說那麼多,真正領悟真空了嗎?明心見性了嗎?各種個體、空間通來通去,究竟是神通還是小鬼通?
《維摩詰經》是典型大乘佛教的經典:特點包括冗長的人物出席表,各種菩薩、天王等;大量人物,幾百萬大眾、菩薩、龍神、夜叉等都來集,滿心歡喜,無不信受奉行。【一時,佛在毘耶離菴羅樹園,與大比丘眾八千人俱,菩薩三萬二千。】《佛國品第一》
包括典型的大乘經文風格,展現各種奇異現象,神通力,在《不思議品第六》中,座椅不夠,於是請須彌燈王佛送來三萬二千大座位放入室內,並讓室內變得寬敞。或《香積佛品第十》,午餐時間,大家為該吃什麼煩惱,於是展現神通,上升去香積佛的國土盛一些飯,順便變出九百萬個師子座位。
可以理解為,那些不是在物質世界中,而是靈性維度的某個界。所以想像都會成為一種現實, 但不代表這些現象在物質世界中可行。真的是天界,或只是一個鬼神界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