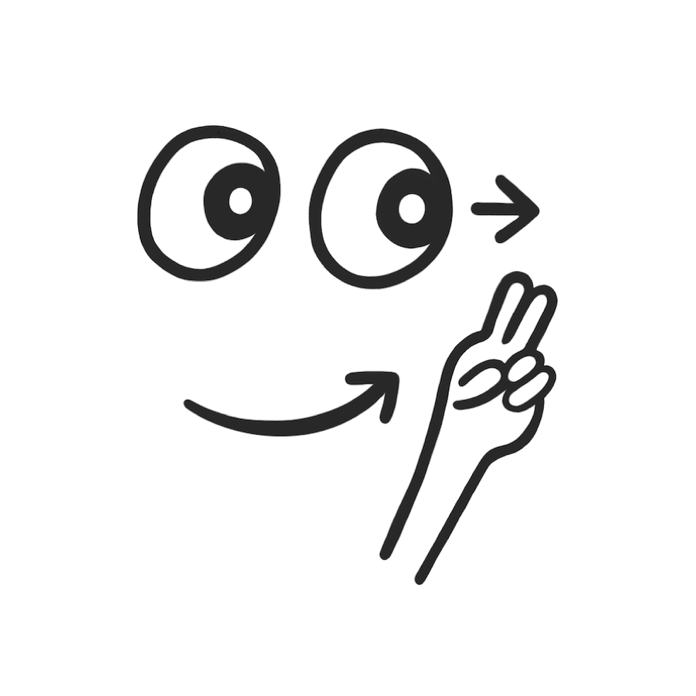《靈性的自我開戰》by Jed McKenna
傑德・麥肯納(Jed McKenna)的《靈性的自我開戰》(Spiritual Warfare)是靈性三部曲中的第三本。
生命的徬徨與掙扎
「我光是通勤就花了十五個多月。我們真正擁有的只有時間,而我就是這樣把它打發掉;把它一點一點切碎,用期待旅程結束的心情來度過。然後在辦公室也是同樣的狀況:從早上八點到晚上六點,盯著時鐘過日子,盼著上午趕快結束好能去吃午餐,又盼著下午趕快過完好能回家。我從未對所在之處感到滿意,總是忙碌、疲憊,又得準備接下來的事情。週末更糟,因為那些週內沒做完的事全得在週末補上。打掃、採購、小孩的事。你能帶小孩做什麼呢?帶他們去一個快餐店裡的遊樂區,給他們吃那些你明知道不好但便宜又甜膩的食物,然後再去逛百貨商場。你想帶他們去博物館或看球賽,可事實上,垃圾食品和購物中心才是真實。丹尼斯週末打高爾夫、看體育節目,因為他得在漫長的工作週後放鬆。他甚至不需要通勤,他的診所在市區。他還覺得我能有那麼多『通勤時間』聽起來不錯呢。」
「我開始注意整個人類運輸系統;我和那幾百個每天見到卻從不交談的人,就像無意識的羊群,帶著各自的報紙、筆電、耳機,來回擺渡。然後我想,整個世界都被困在這台龐大的機器裡,無止境、沒意義地被處理。年紀大的脫落,新的人接上。每天早上,這些金屬管在世界各地運送數百萬人,就像把新鮮血液打進一座座墳場般的城市,晚上再把它們抽出去,帶著骯髒和疲憊。就好像一個被囚禁、失去心智、沒有真正活過、只是在空耗的羊群。每個人都一樣,不只是通勤族;店員、警察、巴士司機、你看到的所有人。你四五歲就被塞進這台機器裡,要到六十多歲才從另一端出來。一旦你看穿這地方就是瘋人院,你就再也無法「不」那樣看。它無處不在,每個人都在裡面。這毫無意義,這不是真正的生活,不可能是。我不知道它是什麼,但肯定不是真正的生活。」
「「那到底是為了什麼呢?」麗莎接著說。「這不是幾個月、幾年的事,而是我們的一生!我們被困住了!整整十五年!這不是很瘋狂嗎?為了什麼?養孩子?那只是個藉口。誰都可以養小孩,不需要讓自己的靈魂一直被碾壓。某天我問 DJ,他想從人生得到什麼?他說想跟爸爸一樣當牙醫。那感覺就像有人狠狠踢了我肚子一腳。」她搖著頭,一臉悲傷。「而且不只是這種生活方式本身很糟,它根本就不算真正的生活。它不是你選的,而是你『沒有選擇』時得到的。我們就這樣毫不停頓地投入這種可笑、荒唐且不可能的生活,也從沒想過自己在做什麼。高中、上大學、讀研究所,然後直接進入職場。結婚、生孩子、借錢、買房,把房子塞滿雜物,再生一個孩子,借更多的錢,買更大的房子,更多的雜物。這簡直是瘋了,但我認識的人都是這樣過。有人稱這叫「Affluenza」(富裕病),就像種疾病。它的確就是種病。過去七年,我們不斷掙扎,只為付上債務的最低付款而已。」」
「我認識的每個人都一個樣。有人收入高一點,有人低一點,但幾乎所有人都在各方面過度透支;金錢、時間、工作、責任。我們做的每件事都在別人看來是『正確』的,而且也沒發生什麼不幸;既無悲劇,也沒健康問題。我們在當地的鄉村俱樂部已是十年資深會員。對,我們活在『美國夢』裡:精疲力竭、身無分文、不是好父母、不快樂,現在還分居了。」
「我寧可化為灰燼,也不願腐朽成塵!我寧可讓我的火花在耀眼的烈焰裡耗盡,也不願被白蟻一點點侵蝕。我寧可當一顆輝煌的流星,每個原子都在絢爛燃燒,而不是一顆昏昏欲睡、永久存在的行星。人類的正當功能是「生活」,而非僅僅「生存」。我不要浪費我的日子,只為延長壽命。我會善用我的時間。」
我是誰?
「除了「I Am」以外,沒有人知道任何事情。沒有任何人或神能聲稱自己知道更多。再多的神明,也不可能存在或被想像,來超越這唯一的認識:「I Am」。」
我們無法知道除了「我」存在這件事以外的任何事。就像問「我是誰?」這個問題其實是無解的,因為你永遠不會真正知道「我」真的是誰,除了知道(I am),知道「我」是一個覺察的意識,一個存在的意識,除此以外,我們的大腦無法理解再理解更多,除非哪一天科學的演進,解開了宇宙被創造出來的謎。
可以嘗試問「我是誰?」,但這個問題的意義並不大,因為只是一種形而上概念的探討,可以覺察到一切都是幻相,一切都不真實,但本質上並不能真正解決生活現實中所面對的困境,好比起伏的情緒、自擾的念頭等。
「所謂成為「開悟」的過程,是個蓄意毀滅自我的行動。是「假的自我」執行那場殺戮,也是「假的自我」死去;除了身體不死以外,其他都等同自殺。因為沒有「真正的自我」來填補那個虛假自我死後留出的空缺,所以最終不再有任何「自我」。因此,我們才說:「無我」才是真正的「自我」。」
這邊再補充一下,傑德所謂的「無我」更多表示瓦解「假我」所產生的認定,但嚴格來說,我們要從兩個層面來探討:一個是形而上,一個是現實幻相中。
釐清這觀念至關重要,如果混淆了,就會陷入身心靈或佛教中所面臨的困境,把一切視為幻象,試圖把一切關空,活在當下,但那只是頭腦的想像。
形而上,跳脫了幻相的投射,這個「我」或「自我」並不存在,所以「無我」。
但現實中,一個人不可能真正「無我」,因為你有一個「我」的主體意識,一個「我」正在覺察、思考。幻相現實中,有一個「自我」,就像灰塵兔的存在,一個人的長相、個性、偏好、文化影響等。
「小我並不需要被殺,因為它從未真正活過。你不需要摧毀一個虛假的自我,因為它不是真實的,這才是重點所在。它只是一個角色,而我們真正需要扼殺的,是那個自以為就是角色的部分。當這部分被消除——真的消除了,這過程可能需要好幾年——那麼,你可以視需要繼續穿那件戲服、演那個角色,但你會同時清楚自己並非角色本身。」
「也許人類最深層的害怕死亡的原因,是我們不知道自己是誰。我們堅信自己擁有獨特、個體且獨立的身份——但如果大膽地去審視,就會發現這個身份完全依賴於一連串無止境的支撐:姓名、個人履歷、伴侶、家人、房子、工作、朋友、信用卡……我們把安全感寄託在這些脆弱易逝的支柱之上。一旦這些都被移除,我們是否知道真正的自己是誰?失去熟悉的支撐,我們就面對赤裸裸的自己,那個我們與之同住一輩子卻從不想面對的不熟悉的陌生人。為了不跟這個陌生人獨處,我們試圖用各種聲響和活動——無論多無聊或瑣碎——塞滿每分每秒。」
瑪雅
「「瑪雅」(Maya)是自我結構的支柱。觀察自我如何運作,研究它,剖析它,逆向工程它。瑪雅既不是一個人、也不是一個概念或女神。除了親身跟她角力,別無他法了解瑪雅的真面目。你不到那深度,就不知她有多深。在這場戰爭裡,瑪雅擁有一切優勢,唯獨缺少一樣:真理。瑪雅並不存在;真理才是真正存在的。」
瑪雅虛假般的存在,卻又如此真實,就像禪宗說的「無門之門」,這些門是如此的虛無,卻又如此的堅實。每一道門,都是我們自己樹立起來的認定,把自己困在假相中。
靈性觀光客
「推動真正覺醒的動力,更像是一種瘋狂。那是一場極度深刻且漫長的危機,不是某些騙子賣給靈性觀光客的「靈魂黑夜」那種無聊小品。」
許多人在尋找心靈的撫慰,尋找圓滿自己渴望的,但那只是跳進自己所構建出來的夢。真相不容許我們想像,也不容許我們討價還價。
「天堂、救贖、慈悲、正念、自我覺察、內在平靜、世界和平、人與人之間的善意……這些都是「安全」又「不麻煩」的靈性目標。它們要求不高,影響不大,跟日常生活式的節奏相容度很高,而且花費也不多。因為這些詞實際上都沒有具體意義,所以也沒有人會太在意是否「成功」或「失敗」。它們也不容易導致狂熱——沒人會以「慈悲」之名去炸巴士——所以也不會落得壞名聲。想達到其中任何一個目標,我們都能覺得自己參與其中:加入某個團體,做些練習,買幾本書,訂閱電子報,或跟志同道合的人聚會,再添置些「靈性周邊」。這些都不會和我們現有的生活條件衝突,很輕易就能融入繁忙的日程表。每天早晚小打小鬧地冥想一下,偶爾週日早上花個鐘頭去教堂,捐款幫助飢餓兒童,閒來翻翻書或偶爾討論兩句,如此就足以撫平我們的「靈性癢」。沒有人會受傷,也不會有人搞出什麼瘋狂事;也沒有人真的會拔掉自己插在大群體中的插頭,獨自走開。偶爾也許有個過度熱情的年輕人跑去禪院,但通常幾年後他會回到俗世,毫髮無傷,或許還會寫本書記錄那段經驗,好讓那幾年不算白費。」
真理的代價是一切
「要完成這種「臣服」的行為,不需要任何信仰或信念,只需要「看清」。當你開始明白自我與恐懼的真實面貌時,整個過程就會像鬆手丟掉重物一樣簡單自然。」
臣服(surrender)這個詞可能很容易誤解,並不是俯首稱臣或屈服於任何人事物,但必須止息頭腦來覺察、來聆聽。否則很容易困在我們所說的思維模板裡面打轉,跳不出過去建立起來的認定。
「遺憾的是,由於通俗基督教、監獄中臨時「悔改」、以及「十二步驟」等所推廣的「假臣服」,使得這一關鍵且必要的成長階段名聲受損,並被普遍視為懦弱者、愚蠢者或恐懼者在絕望中所做的行為。這正是瑪雅(Maya)在世間運作的明顯示例。」
許多人尋找覺醒,雖然理解很多靈性的概念,但沒有意會到自己被困在自己的認定框架裡,嘗試用自己過去的知識來詮釋什麼叫做覺悟,去理解一個完全不同範式的覺悟概念。
「真理的代價是『一切』,真理的代價也是『無』。」這正是「無門之門」悖論的另一種說法。
但所謂的一切並不是拋棄家庭、拋棄錢財,那些是錯誤的觀念,哪些仍是身外之物,真正的代價是你一切的認定。像是禪宗《達摩血脈論》說的:「但有住著一心一能一解一見,佛都不許。」
「「想要」或「選擇」靈性開悟,並不可能是出於知情的選擇。渴望開悟,就是對它的誤解。小我不可能渴望「無小我」。人不會是出於對真理的熱愛而踏上覺醒之路,而是出於對虛假之深切厭惡;一種強烈到可以燒毀一切、不留餘地的憎惡。」
問對問題
「「靈性自體解構」(Spiritual Autolysis),過程的重點不在於尋找「答案」,而在於尋找正確的「提問」。因為根本沒有可找到的「答案」,只有那些「問題」在框定我們的局限。當你理解了那個問題,你便打破了那層侷限。也唯有透過大無畏的思考與看清,才能摧毀幻象。」
比起得到答案,更重要是問對問題。因為每一個問題都會有一個前提,這個前提是什麼?為什麼你會問這個問題?可以往回拆解,找到問題的前提。
覺悟,出獄了
「就是這種感覺;一片麻木,好像我剛剛出獄一樣。過去十五年,就像渾渾噩噩地過去,我總是疲憊、焦慮、忙碌。如今一切突然終結,我不知道該做什麼、該去哪裡、該成為誰。」
我在到達時,也有類似體會,沒有了過去的束縛。現在我是一個自由人了,我想要做什麼?
愛麗絲來到岔路前,問貓:「我該走哪條路?」
貓回答:「那要看你想去哪裡。」
「我不知道我要去哪。」愛麗絲說。
「那麼,」貓答,「走哪條路都無所謂。」
一場戲
「宇宙是純粹的智慧:絕對、毫無差錯、完美無瑕。那海洋、星辰、微觀世界與你之間的差異何在?只有「小我」。只有小我披覆的存有才會顯現不完美與愚蠢,愛與恨、欣賞與恐懼、藝術或種族滅絕……以及我們最關心的「超越」能力。我們可以超越自我程式的設定,回歸整合狀態。
從更高角度看,所有的「錯誤」都只是一部分的完美——我們不過是在一個子系統裡。從外面看,那仍是完美。我們是完美中帶著不完美,天生具有缺陷的設計。當我們放下小我對事物好壞的評判,就會看到:唯一能評斷事物的標準,是「它是否發生」。如果那異端真的犯了異端言論,那麼群眾把他火刑處死也是順理成章;沒有對錯、善惡,只有「有或沒有」。任何發生即「正確」。這世界的一切,都在這「最好的可能世界」裡展開。」
這一段的解釋不是特別完整,加註一下。這宇宙並不「完美」,只能說就像一場電影,情節可能極度荒謬。一場戲,你可以喜歡或不喜歡,但本質上沒有對錯之分。電影劇情中,有是非善惡,但跳出電影外,則沒有是非善惡,你無法批判情節中人事物的「對錯」,因為戲就是這麼演,就是戲劇的本質。所以覺醒的重點就是明瞭這場劇的虛幻本質而跳出來,不再陷入情節中打轉。
「你不需要相信別人不會背叛或傷你,你只要相信他們會是『他們自己』。只要你看清恐懼是怎麼回事,就能理解一切人的行為:在閉眼者的世界,所有的行為本質上都源自恐懼,無論是好是壞、勇敢或怯懦、愛或恨,全都來自同一口井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