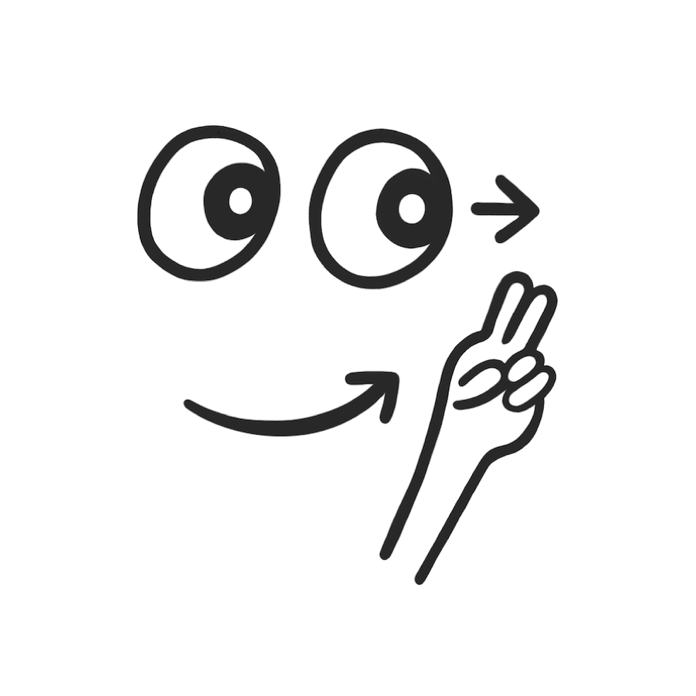解析《大佛頂首楞嚴經》
《楞嚴經》的開頭,阿難在乞食途中,經過了一處淫室,被摩登伽女以外道梵天咒所攝,引誘進淫亂之處,並被撫摩誘惑。佛陀放射寶光,宣說神咒。使那邪咒破除,並結集大眾進一步開演三摩地之真實義。
誠實地說,楞嚴經的東西繞來繞去,繁冗複雜,實在很難看懂究竟要表達什麼,感覺是解文字謎,整本的花巾結。
卷一
盲人與黑暗
【佛告阿難:「汝言相類,是義不然。何以故?如無手人,拳畢竟滅;彼無眼者,非見全無。所以者何?汝試於途詢問盲人:『汝何所見?』彼諸盲人必來答汝:『我今眼前唯見黑暗,更無他矚。』以是義觀,前塵自暗,見何虧損?」阿難言:「諸盲眼前唯覩黑暗,云何成見?」佛告阿難:「諸盲無眼唯觀黑暗,與有眼人處於暗室,二黑有別、為無有別?」「如是,世尊!此暗中人與彼群盲,二黑校量,曾無有異。」「阿難!若無眼人全見前黑,忽得眼光,還於前塵見種種色名眼見者;彼暗中人全見前黑,忽獲燈光,亦於前塵見種種色應名燈見。若燈見者,燈能有見,自不名燈。又則燈觀,何關汝事?是故當知,燈能顯色,如是見者是眼非燈;眼能顯色,如是見性是心非眼。」阿難雖復得聞是言,與諸大眾口已默然,心未開悟。】
佛告阿難:「你說這是相同,但義理不是這樣的。為什麼呢?因為無手之人,但沒有拳,但無眼之人,並不是能見之體全無。」
這是什麼緣故呢?你若不信,可試於路途中,詢問盲人:『你現在看到什麼?』他們一定會說:『我眼前只是一片黑暗,沒有看見其他。』所以,他們眼前『見到』的也是黑暗。對於盲人而言,前塵雖是黑暗,他們的見性何曾壞滅?」
阿難:「盲人眼前只有黑暗,怎麼能算是看見?」
佛告阿難:「盲人無眼只能見黑暗,和有眼人在黑屋子裡見到的黑暗,這兩種黑暗有什麼不同嗎?」
阿難:「確實沒差,世尊!一個在暗中,一個是天生盲;兩者同樣都是覺得只見黑暗。」
佛陀:「那麼若無眼之人,眼前見到一片漆黑,倏然得眼力,就能看見種種色相,名為『眼見』;在暗室裡的人,也忽然獲得燈光,就能看見種種色相,難道能說是『燈在見』嗎?如果真是『燈見』,燈就成了能見,那就不叫燈了!而且燈自己去看,與你有何關係?
所以,你要明白:燈只是顯色;眼能顯色也是基於見性,但能見的根本是『心』,而非單單眼根。」
阿難聽完不理解,大眾也沒言語,期待佛再為他們闡明。
註解:
百寶輪掌,開開合合
當下如來在大眾裡,屈起五指,開合幾次,問阿難:「你現在見到什麼?」
阿難:「我看見世尊百寶輪掌,在眾人面前開開合合。」
佛問:「你看到我手眾中開合,是因為我的手本身開合?還是因為你的『見』本身在開合?」
阿難:「這是如來您的寶手開合,我的見性並沒有開開合合。」
佛說:「那麼究竟是誰在動、誰在靜?」
阿難:「佛手一直在移動,而我的見性還沒有靜下,哪來的『無住』或『不動』?」
佛說:「就是這樣。」
接著如來於掌中放出一道寶光飛到阿難右邊,阿難就把頭轉向右;又放一道光到阿難左邊,阿難又轉頭向左。
佛問:「阿難,你的頭今天怎麼跟著晃?」
阿難:「我看見如來放寶光在我左右,所以我左右觀看,頭自然跟著擺動。」
佛陀再問:「是你的頭動,還是見在動?」
阿難:「是我頭自己動了,而我的見性本無止息,談不上搖晃!」
佛陀:「正是如此。」
註解:
卷二
阿難頂禮佛陀,說:「若這見聞真是不生不滅,世尊又怎說我們失了真性,做顛倒事?願佛慈悲,替我等洗盡疑惑。」
佛回答阿難的疑問,舉手作為譬喻:如來垂金色臂,手指向下。問阿難:「這是正?還是倒?」阿難答:「世人都認為這樣是倒,但我其實不知孰正孰倒。」
如來又垂臂轉為上指,接著問:「那世人就稱之為『正』了?你可細思:眾生見此倒與正,可知自身若比諸佛清淨法身,就是『顛倒』?因為如來的身是正遍知,汝等之身是性顛倒。可你們仔細觀察,你們究竟哪裡顛倒?」
阿難和大眾瞠目看佛,不知顛倒之處。
註解:
卷三
一切「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」其實都只是「如來藏妙真如性」的幻化。一離「妙心」,六根六塵六識無所依託,就像鏡花水月。表面上的見聞覺知,山河大地、五大、虛空,皆是隨業顯現的妄相;離開如來藏性,一切法都無所依憑,不可得。
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「六入」的「見、聞、嗅、嘗、覺、知」,其實都依賴「妄塵」才能顯現。
在「六入」的基礎上,佛再把「根」與「塵」合起來講成「十二處」:眼、色;耳、聲;鼻、香;舌、味;身、觸;意、法。釋迦再度論證:眼、色合生見性,耳、聲合生聽性……都找不到「究竟來源」,「十二處」也只是「妄想」罷了。
接下來,再把「六識」加進去形成「十八界」,分析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」與「根、塵」三者間的關係。最後,總結:這一切都是眾生的「識心所分別計度」,不真實。
註解:
卷四
先略過。
卷五
花巾比喻「結」
佛陀站在師子座上,召集了出家的僧眾,拿起七寶所製的花巾,並開始將花巾挽成一個結。佛陀問阿難:「這個結叫什麼?」阿難和眾弟子答:「這叫結。」接著,佛陀又繼續綁了幾個花巾結,反覆問,眾人都答:「結。」共打了六個結。
佛陀問阿難:「我挽上第一個結時,你說這是結,這條花巾本來只一條,那麼在挽第二個結第三個結時,你們為什麼又叫這些是結呢?」阿難回答:「世尊,這條華巾雖然它本來只是一條,但挽了一次,就有了一個結的名稱。如果挽上一百次,就會叫做一百個結。何況這條華巾只有六個結,既不夠七個結,也不是五個結,如來為什麼只認為第一個結叫做結,其餘第二、第三等不叫做結呢?」
如來告訴阿難:「你知道這條寶巾本來只是一條,而我挽了六次所以認為有六個結。你再審察詳觀,這寶巾單純沒有異體,挽上結以後才有了異樣,這什麼意思?最初挽上結時,叫做第一結,這樣一直挽到第六個結時,我卻要把這第六結叫做第一結,這樣行嗎?」
阿難回答:「這樣不行,如果挽了六個結,第六個結只能叫做第六結,不能叫做第一結。既使傾盡辯才,也不能弄亂這些結的名序。」
如來說:「沒錯。六個結雖各不相同,但本來都是一條華巾而來的,只是打了六個結,名有六結。但它們名序雜亂是不行的。你的六種根塵也是這樣,本來在相同中產生差異。」
如來又對阿難說:「你一定不喜歡這六個結各異,希望它只是一個單純的結,但怎樣才能恢復這一個結的單純本體呢?」阿難說:「六個結如果存在,就會產生是非:此結不是彼結,彼結不是此結。問題不能停息,如果如來把這六個結一併解除,那麼,沒有了結也就沒有了此結彼結的爭鬥,第一個結都沒有了,怎麼會有第六個結?」
如來說:「我所說的六根解脫一根亦無的道理也是這樣。從極遠極遠的無始以來,心性狂亂,生出了無明妄亂的知見。如此妄亂知見相生相續,不能停息,於是勞與見引發塵相,執取心外塵物。猶如眼睛疲勞,湛明虛空中無由看見亂花狂飛。一切山河大地,以至於生死涅槃,都是因為狂勞而生的顛倒。」
【阿難言:此勞同結,云何解除?如來以手,將所結巾,偏牽其左,問阿難言:如是解不?不也,世尊;旋復以手,偏牽右邊,又問阿難:如是解不?不也,世尊。佛告阿難:吾今以手,左右各牽,竟不能解。汝設方便,云何解成?阿難白佛言:世尊!當于結心,解即分散。佛告阿難:如是!如是!若欲除結,當於結心。阿難!我說佛法,從因緣生,非取世間和合粗相,如來發明,世、出世法,知其本因,隨所緣出。如是乃至,恒沙界外,一滴之雨,亦知頭數;現前種種,松直棘曲,鵠白烏玄,皆了元由。是故阿難!隨汝心中,選擇六根,根結若除,塵相自滅,諸妄銷亡,不真何待?】
佛陀拿起那已綁好的花巾,用手偏向左邊扯了扯,問阿難:「這樣扯,能解開結嗎?」阿難回答:「不能,世尊。」
佛陀又把巾往右邊扯,問阿難:「這樣解得開嗎?」阿難:「也解不開,世尊。」
佛陀:「我試著左右兩邊牽動它,還是沒能解開。你想想,有什麼方法能把它解開呢?」
阿難:「世尊,應該要『對準結心』去解,就能鬆開結。」
佛陀:「說得對,要把結解開,一定要從結的中心去解才行。阿難,我所說的法是從因緣生出的,但不是取世間法的因緣和合,感官所感知的『粗相』。如來闡明『世間法』和『出世法』,知道什麼『因』而來,知道『隨』什麼緣而生。甚至知道恆河沙數般多的世界外,一滴雨的數量。明白眼前的種種現象,明白松樹為什麼是直的,荊棘為什麼是彎曲的,鵠鳥為什麼是白色的,烏鴉為什麼是黑色的,都能知道由來。所以,阿難,隨你的心意選擇六根中的一根來修証,只要一根解除,解開根結,一切妄想塵相自然消滅,真實的不顯又待何時?」
【阿難!吾今問汝:此劫波羅巾,六結現前,同時解縈,得同除不?不也,世尊。是結本以次第綰生,今日當須次第而解,六結同體,結不同時,則結解時,云何同除?佛言:六根解除,亦復如是。此根初解,先得人空;空性圓明,成法解脫,解脫法已,俱空不生。是名菩薩,從三摩地,得無生忍。】
佛陀說:「阿難!我現在再問你,這劫波羅花巾上現前的六個結,在同一時間結成的嗎?能否一次就全部解開?」
阿難答:「不會同時解開,這六個結,本來也是依著次第一個個綁起來的。如果要解開它,就必須逐一解開。雖然是同一塊巾,但結畢竟不是同時形成的,解結時又怎能一下子全部同時解散呢?」
佛陀說:「六根的解脫也是同樣道理。根結解開之初,可獲得離塵除垢根塵消盡的『人空』。空性本來圓明,獲得人空後,繼續解結,再悟『法空』,解脫了法執;得獲法空,當『解脫法』都不復執取,一切生滅皆不再生起,這就叫做菩薩於三摩地中得『無生忍』。」
註解:
佛陀教導從起初領悟「人空」,到「法空」,到最後證得「無生忍」,也譯為「無生法忍」。起初不再執著於「自我」,認識「自我」只是暫時性的因緣和合;進而領悟「法空」,一切事物、一切現象皆空;到最後的「無生忍」,安住於『無生』,一切現象都不曾真正出生或消失,都是緣起而幻現。
但活在這現實中,你有這具身體,不可能將一切化空,所以不可能有所謂的「人空」。
二十五種解脫方式
佛陀問眾多菩薩及阿羅漢,誰能證明自己如何從這些執著中解脫,得到了圓通與解脫。「你們這些大菩薩與阿羅漢,既然在我法中已證『無學』,我想請問你們:最初發心觀照『十八界』時,各自是依何門得悟?又是從哪種方便而進入『三摩地』的?」
眾弟子分享各自的修行體驗,所證得的境界:
我聽聞佛陀說法的『音聲』中悟入四聖諦。
我觀修不淨相,生厭離,觀察不淨、乃至白骨、微塵,而歸於虛空,體會空與色都不具自性,悟入『色』的實相。
我回到房舍中修行時,看到幾位比丘燃起沈水香,香氣靜靜地進入鼻中。於是觀察這『氣』,既不在木頭裡,也不在虛空中,不是煙,更不是火,離去時無所依,飄來時亦無所從。藉由這般觀察,內心妄念自消。
我觀『味性』,酸、苦、鹹、淡、甘、辛等味道,既非空也非有,不即身心也不離身心。
觀『妙觸』,洗澡時,忽然明白了『水』的因緣:它既不是真正能洗滌外在塵垢,也不是真正能洗滌身體;於其中安住自在,心念不著於有無。
觀察世間『六塵』不斷生滅變壞,就專修『空寂』的法門。
我初出家時,常常昏沈好睡,曾被佛陀訶斥為畜生類。我聽到佛陀的責備以後,悲痛啼哭,便七天不眠,導致雙目失明。世尊於是為我開示,使我不藉眼睛,能見十方境界,清晰透徹,就如觀掌中之物般明白。
專注觀察呼吸的細微變化,甚至窮盡『生、住、異、滅』四相,了了分明地看到『諸行』剎那生滅。
我過去劫中戲弄出家沙門,導致口業纏身,世世生生患有像牛反芻一樣的毛病。佛陀為我開示一味清淨心地法門,使我得以滅除雜念而入於三摩地。
『世間的種種境遇,不可貪樂』。有一次,我進城乞食,邊走邊思惟法門,沒留意到路上有毒刺,結果刺傷了腳,全身疼痛。我心裡察覺『痛』之所在,也覺知那份『知道痛』的覺性。即使是在疼痛之中,我依然觀察那『能覺』的心是清淨、沒有苦痛的。我又進一步思惟:『同在一個身上,怎麼會出現「痛覺」和「無痛之覺」兩種呢?』剛凝神觀察不久,身心忽然空寂。經過二十一天的專注修行,我所有的煩惱、漏障都滅盡,成就阿羅漢果。
我在無量劫以來,心念無礙,也能回憶自己經歷過恆河沙數那麼多的生死。自我投胎到母腹開始,就常能體悟到『空寂』之理,乃至於觀照十方皆空,並令眾生也能證得空性。
以『清淨的心見』為本。無論世間或出世間的一切境相、變化,我只要一見就能洞然通達,無有障礙。
『普賢行』我以用心聽聞眾生的一切知見。
令我『觀鼻端白』。我依教奉行,專心觀察二十一天,親見鼻中氣息出入如煙,於是身心內外通明,整個世界都變得清淨,猶如琉璃一般。之後,那煙相漸漸消失,鼻息化為清淨白色,我的心慧因此開朗,煩惱漏盡。
常常宣說『苦、空』之理,深達諸法實相。
我親身跟隨佛陀離開皇宮出家,親見佛陀六年勤苦修行,親見佛陀降伏諸魔外道,斷盡世間貪欲煩惱漏。承蒙佛陀教授戒律,我親身受持,於是身心寂滅,證得阿羅漢果。佛陀在大眾中任命我為紀律的榜樣,以『持戒修身』。
聽解說『因緣深義』,於是我豁然開悟,得到大通達。
一尊佛告誡我:貪淫過盛的人,猶如沸騰火聚,最易燒身,並教授我『遍觀身中百骸、四肢,以及冷暖諸氣』的法門。我觀察自心光明凝注,全力銷熾貪欲,將其化為『智慧之火』。
每逢妨礙車馬通行的坑洼,我都加以平整,建築橋梁,背負沙土,勤苦不輟。有人需要幫忙扛運貨物,我也主動代勞,不取任何酬勞。國王迎請佛陀設齋時,我就在行經之處平整土地。當時,毘舍如來摩我頂,告訴我:『你若能平伏自心之地,則整個世界之地也就平了!』我豁然開朗,看見自身微塵之體與造成世界的微塵不差分毫。
觀照自己身中的『水性』,從涕、唾等分泌開始,乃至津液、精血、大小便利,都是『水』這一性質;體會到身中的水流,與外在世界的一切海洋,其性無有差別。我那時『水觀』能見身如水。有一天,我入禪定時,恰好有一位小沙彌從窗戶往裡窺看,見整個屋子中遍滿清水,不見我身,童子好奇地拿了一塊瓦礫丟進水裡。我出定後,突然感覺心痛,猶如舍利弗被『違害鬼』所傷一般。我非常疑惑:『我已經證得阿羅漢道,向來不會無端生病,何以今日竟突然心痛?莫非修行退失?』這時,那童子跑來向我陳述他剛才所做的事。我就告訴他:『你再回去看看,若還見滿屋清水,就打開門走進水中,把那瓦礫取走。』童子聽從教誨,再度見屋內充滿清水,瓦礫果然還在其中,於是打開門、入定除去瓦礫。我出定後,身體便恢復如初。
我觀察此世界及眾生色身,皆是種種因緣妄動,如風力所轉。當時,我專心觀察世界如何搖動、身體如何動停、心念如何生,發現這些動相毫無差別,都是依妄而生。領悟十方微塵以及無量顛倒眾生,都是同一虛妄。三千大千世界中的所有眾生,猶如小小器皿裡的蚊蚋,發出狂亂的嗡鳴,無休無止地鼓噪。
我手持四顆大寶珠,放光照耀十方微塵佛剎,使之化為虛空。我諦觀『四大無依』、妄想生滅而本自虛空,故佛土、虛空,本是一體。
『唯心識定』,令我入三摩地。使『貪著世名』的心漸漸止息。
『念佛三昧』:假設有兩人,一人專心思憶,另一人卻完全遺忘。如此二人即使相逢,也形同不逢;或見猶如不見。若兩人都彼此惦念,憶念之情深刻,甚至生生世世也如形影相隨,絕不分離。十方如來憐念眾生,就像母親思念兒子;但若兒子遠逃,母親即使思念,也無濟於事。若兒子也能憶念母親,如母親憶子一般,那母子就生生世世不會相違。同理,若眾生一心憶佛、念佛,現前或未來都必定能見佛,離佛不遠。
註解:
卷六
觀世音菩薩敘述得道因緣
觀世音菩薩向佛陀說:「世尊!我回想在非常久遠,如恆河沙那樣多的劫數以前,有一尊佛出現在世,名叫『觀世音』。我在他面前立下大願,想要成佛度眾生,並依照他的教導,從『聽聞』下手,不斷思考、修行,最後進入三摩地。
起初,我專注地聽,一心一意,把注意力放在『聽』這件事上,逆著外在的聲音之流,把心往裡收攝,慢慢地放掉外面的聲音。隨著專注越來越深,到了極致時,進入一種『入流』。彷彿忘了自己是誰在聽,只剩下專注本身。接下來,進入一種非常寂靜的境界,不受外界聲音所擾。我依然保持清楚,但心不被外境攪動。
繼續修行,慢慢地連『能聽的人』和『所聽的聲音』都消失了。不但聲音不見了,連那個「正在聽」的念頭也沒有了。更深的覺知,連「空跟能空」這種對立概念都不再存在。所有生滅、變化的感受都停止了,最深沉的寂靜就顯露出來。我在那一刻,突然感覺超越了一切境界,彷彿十方世界都明明白白。
透過這種修行,我得到兩種很大的收穫:
能和十方諸佛的本初覺性完全相應:也就是能和佛陀同樣擁有那份深切的大慈悲力。
能和十方六道眾生同一悲心:也能感受到、體貼到所有眾生的苦難而生起深切的大悲憐憫。
註解:
上述的經驗其實就是「靈性經驗」,並不會因此解脫成就。如果冥想時能進入很深的意識改變狀態,就可能出現類似的感受,我也感受過類似的經驗。
這也類似老子的「致虛極,守靜篤。」或是莊子的「坐忘」,進入深沉的冥想意識狀態,一切事物開始消失。在《莊子·大宗師》中:
顏回曰:「回坐忘矣。」仲尼曰:「何謂坐忘?」顏回曰:「擲肢體,黜聰明,離形去知,同於大通。此謂坐忘。」
四種「無作妙德」
觀世音菩薩說自己修習「圓通」,證得無上道,可以示現四種不可思議的無作妙德:
初獲妙妙聞心:獲得「微妙的聽聞之心」,心中雖有「聽」,卻不執著於聲塵,因此「見、聞、覺、知」不再彼此割裂,成就了一種圓融清淨的寶覺。所以,我(觀世音)能顯現許多不可思議的形象,也能說出許多祕密神咒。比方說,我可以示現一首、三首、五首,乃至成百上千、八萬四千個頭;或者二臂、四臂,甚至八萬四千臂;或二目、三目,乃至無數目;或展現慈悲相、威猛相、禪定相、智慧相,隨機救護眾生而得大自在。
2. 由聞思修脫出六塵:犯境時如聲音能「穿透牆壁」,不被阻礙;我顯現任何一種形身、誦持任何一種咒語,都能讓眾生得無畏。故十方所有國土的眾生,都稱我為「施無畏者」。
3. 修習本妙圓通清淨本根:所到之處,眾生都願意捨棄一切財物珍寶,祈求我大悲憐愍。
4. 得佛心印,究竟圓滿:能以種種珍貴之物供養十方如來,也同時布施六道眾生:有人想求妻,可得好姻緣;想求子,便能生子;求三昧,能得三昧;求長壽,能得長壽;乃至追求大涅槃,也能成就大涅槃。
註解:
首先,「凡所有相,皆是虛妄。」示現形象並不代表什麼,魔王也可以示現慈悲相、威猛相。第二,八萬四千個頭,八萬四千臂,豈不是妖怪?
「所到之處,眾生都願意捨棄一切財物珍寶,祈求我大悲憐愍。」和「求妻,得好姻緣;求子,能生子;求三昧,能得三昧;求長壽,能得長壽。」
實在不知道怎麼形容這種情況,所以問 ChatGPT,它說:「若單就字面而言,也可能是某些民間修行者(或自稱「神祇降世」)在誇大聲稱自己「能普予一切」;多半是個人妄語或扮演神跡角色。真正的大菩薩或如來,雖然有大神力,卻絕非隨意以「顯靈換財物」的方式示現,而是為令眾生離苦得樂、信受正法。」
文殊師利稱頌觀世音的「耳根圓通」法門
《楞嚴經》中,佛陀邀請二十五位菩薩介紹各自證悟的法門。但經文中有一篇長偈,其中文殊師利評述「二十五圓通」的修行法門的不足之處,唯獨稱頌觀世音的「耳根圓通」法門最契機、最為殊勝。「佛出娑婆界,此方真教體,清淨在音聞;欲取三摩提,實以聞中入。」他說「反聞聞自性,性成無上道。」是微塵數佛所共開示的成佛之道。
以下是文殊師利在偈中的評論:
「色塵:妄想執取造成表面可見,若看不穿其虛妄,就無法真正通達。音聲:帶著語言、名相,只能表達局部意義,難以圓滿顯示真理。香塵:必須靠接近才能嗅到,一旦遠離便失去作用,不夠恆常。味塵:唯有入口時才生味,瞬間又消失,使覺知無法長久安住。觸塵:得藉接觸才有感,一旦分開就無,顯示其非安穩常存。法塵:源於意識概念,若無能知、所知,立刻不復存在,終究難以遍通。從這些特性看來,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各有侷限,無法抵達究竟的圓通之境。」
「眼根雖能看得清楚,卻只能向前看,無法遍及四面八方,侷限性明顯。鼻根只有呼吸時才感受出入,不是隨時都能涵蓋一切境界。舌根必須依賴味道才生覺受,味消則覺失,根本不恆定。身根要靠接觸才能知,身與境各有範圍,也無法進入無量覺觀。意根雜念紛飛,生想起念,既然還難脫妄想,又怎能究竟圓通?」
「識體本身混雜於眼耳鼻等根,究其根源並不穩定,難以成為究竟依憑。心聞十方雖顯現大境界,卻需要深厚因緣,初心者難以相應。單純觀鼻端等,只是暫時收攝心念的巧法,一旦執著『住處』反會成障礙。以口說音聲度眾,其名相不離有漏,若生執著便不是真圓通。守戒與犯戒只與身行相關,不足以遍及一切處。神通則憑宿世福報與外境相緣,不等於究竟的無漏慧;因此,上述這些都無法真正證入圓通。」
「以四大(地水火風) 或空、或識」為入門修行的不足:『地、水、火、風』:各有其對待(堅、濕、熱、動),不是真正的究竟無對。『空』:本身帶有昏寂一面,缺乏覺照。『識』:又是生滅不住。因此,都不能算作最穩當、最究竟的「圓通」。」
註解:
經文的矛盾,卷五中,那25個菩薩分享各自成就的方式,達到三摩地,達到阿羅漢果。但除了觀世音,其他全部被文殊師利否定了,那些修行方法是否有用?
三無漏學:先戒後定,因定生慧
佛陀告訴阿難:「你常聽我在毘奈耶(戒律)中開示:若要真修行,必須先從『三個決定義』下手,即『攝心為戒、因戒生定、因定發慧』,這就是所謂的『三無漏學』。
【若諸世界六道眾生,其心不婬,則不隨其生死相續。汝修三昧本出塵勞,婬心不除,塵不可出。縱有多智,禪定現前,如不斷婬,必落魔道。】
釋迦牟尼說:「所謂『攝心為戒』,首先要斷除「婬心」。所有六道眾生,只要仍然迷戀婬欲,就永遠脫不了生死。而你們修三昧(禪定),本來是為擺脫「塵勞」(煩惱)而來,倘若婬心不除,連世間塵勞都拔不出,更別說證得出世間的解脫。就算你很有智慧,或者能坐出禪定境界,如果不斷婬欲,最後都會墮入魔道。
註解:
性慾只是自然的生理作用,生物繁衍交配的動機,只是如果縱慾,把性慾弄得複雜,衍生了亂象。但不需要將性本能劃入罪惡的範疇,認定慾望是萬惡之源。
所以《達摩血脈論》說:
「在家人有妻子,淫慾不除,可以見性嗎?」達摩答:「只探討是否見性,而無關乎是否有淫慾。淫慾本來就跟幻相一樣虛幻不實,自然斷除,若不沉溺,縱使有習氣,也不妨礙。為什麼?自性本質是清淨的。雖然處於肉體中,但自性本質清淨,無法被玷污。法身,本來的自性,無飢渴、無寒熱、無生老病死、無恩愛、無眷屬、無苦樂、無善惡、無長短、無強弱,本來無有一物可得;只因緣和合有此肉體,才有了飢、渴、寒、熱、瘴、病等身體現象,若不執著,自由運作。」
六祖惠能也給予了相同的答案,「若見自心是佛,不在剃除鬚髮,白衣亦是佛。若不見性,剃除鬚髮,亦是外道。」
因戒生定:斷除殺生
佛陀接著說:「若懷『殺心』,便無法真正脫離生死輪迴。就算有人多智多定,不斷殺也只能墮入神鬼道。我涅槃後,末法時代會有神鬼興盛,甚至主張『吃肉亦能成菩提』。
我先前允許比丘食『五淨肉』,其實是憑我神力幻化,並不是真有眾生可殺。等我滅度後,如果有人仍吃眾生肉,卻自稱佛弟子,將來必墮羅剎道,哪怕坐得一點定力也屬魔道,無法脫離生死。
真修行的大悲者,甚至走路都盡量不傷草命,何況以血肉為食?更有比丘連絲綿、絹帛、皮鞋、裘衣、乳酪、醍醐等動物產物都能捨不使用,才是真正遠離對眾生生命的侵犯。這樣的開示才是『佛說』;不然即是『魔說』。
註解:
《達摩血脈論》
問曰:旃陀羅殺生作業,如何得成佛?
答曰:只言見性不言作業。縱作業不同,一切業拘不得。從無始曠大劫來,只為不見性,墮地獄中,所以作業輪迴生死。從悟得本性,終不作業。若不見性,念佛免報不得,非論殺生命。若見性疑心頓除,殺生命亦不奈它何。
因定發慧:斷除偷盜
必須斷除偷盜的心。若帶著僥倖貪求,想藉禪定超脫塵勞,最終只會落入邪道。末法時代,這些妖邪往往假裝善知識,暗地裡騙財騙色,令眾生家破人亡。
當年我教比丘們『循方乞食』,也就是不揀擇布施者、不貪求美味,捨去貪念,成就菩薩道。所以比丘也不該自己煮食,意在寄生三界、隨處行化,示現人生不應久住。
若在我滅度之後,比丘真想修三摩地,可以做大布施、燃燒一指節、燃身上香疤,馬上可還清無始以來的宿世業債;這樣未必馬上證無上覺,至少決心不退轉。如果連這一點小小棄捨都不肯做,就算有得「無為」境,依舊可能要生在人間繼續還債,如佛陀吃馬麥。
不斷除偷盜而想修定,就像用有裂縫的器具盛水,怎麼灌都是漏空。真實的比丘,除了日常必要衣鉢之外,分寸不多佔;所乞的剩餘飯食也分給飢餓眾生。遇人辱罵或讚歎都看成相同待遇;甚至身心也可捨,骨血也可分給眾生,內外都毫無貪藏。
註解:
「燃燒指節、身上燒香疤」其實很荒謬,這樣就能還宿世業債?捨身心,這些都跟見性解脫毫無關係。
大妄語
第四條:如果還有『大妄語』,哪怕前面已守不婬、不殺、不盜,也無法得清淨三昧,反而變成愛見魔,斷『如來種』。
『大妄語』就是明明沒證聖果,卻誆稱自己已經是某種聖者,或為博得名利騙取眾生供養,等同斷自善根、墮入苦海,不能再得正定。
我滅度後,菩薩或阿羅漢會在末法示現各種身分——沙門、居士、國王、官員,甚至婬女、寡婦、屠夫等,混跡人間度眾,但他們都不會自封『真菩薩、真羅漢』或隨意揭示佛的祕密法義。
說謊修行,猶如把糞當作栴檀,怎可能有香氣?誠實修行的人,在行住坐臥中都無虛假,絕不自譽得高妙境界,就好比窮人謊稱自己是國王,終會自招禍患。因地若不誠實,果報必定扭曲。
卷七
儀軌壇城
佛陀為阿難及末世眾生,詳細闡述「如何設立清淨道場、結界修行」,從選地、築壇、供養、護法、懺儀到最終三七日、乃至百日的行持,讓有志修三摩地者能藉此得佛加被、成就正定。
佛陀詳細說明如何築壇、結界:
清淨場地
先去尋找『雪山大力白牛』的牛糞。因牠們只吃雪山上的肥嫩香草,也只喝那裡的清淨雪水,所以牠的糞便極為純淨微細,可以拿來和上栴檀粉『抹壇地』。如果不是雪山牛,那糞便就不乾淨,沒辦法塗用。
或者,你在平原上,挖下五尺深,取那黃土與栴檀、沉水、蘇合、薰陸、鬱金、白膠、青木、零陵、甘松、雞舌(共十種香料)一同磨粉,調和成香泥,來塗抹場地。
壇的形制
範圍要方圓丈六,並且做八角壇。壇心擺放一朵蓮華(可用金、銀、銅、木製成),蓮華中安一個盛水的鉢。那鉢裡先盛「八月露水」,裡面隨意再放些花葉。再取八面圓鏡,分別安在八個方位,圍繞花鉢。鏡外再設十六蓮華座,以及十六個香爐,花瓣鋪陳其間。香爐裡唯燒沉水香,且不令外見火焰。
供品
用白牛乳盛於十六個器皿;以此乳做餅,亦備沙糖、油餅、乳糜、酥合、蜜薑、純酥、純蜜、以及各種果子、乾鮮葡萄、石蜜、乃至種種妙食。一共十六份,圍繞花外,奉給諸佛菩薩。
如果是在深夜供食,取半升蜜、三合酥,在壇前另設一小火爐,燒兜樓婆香,再把酥蜜投入炭火中,燒到煙盡,作為供養。
壇的四周懸掛幡花;又在壇室四壁供奉十方如來及菩薩像。在正面安放盧舍那、釋迦、彌勒、阿閦、阿彌陀,並觀音菩薩、金剛藏等。
帝釋、梵王、烏芻瑟摩、藍地迦、軍茶利等,以及毘俱知、四天王、頻那、夜迦等像,都張掛在門側兩邊。
另取八面鏡子,懸於虛空,與壇場中的鏡彼此相對,使鏡影層層相涉。
七日懺儀
第1個七天,要至誠頂禮十方如來、諸大菩薩與阿羅漢,六個時段不斷誦呪,繞壇行道,一次繞壇誦呪108遍。
第2個七天,專心發菩薩願,心中不斷。佛律已經明白指示此種願行方式。
第3個七天,每十二個時段都專持『佛般怛羅呪』。至第7日,十方如來同時現前,鏡交光處,諸佛為你摩頂加被,便能在此道場中入三摩地。
如此,末世修行者身心清明,好比琉璃。
若此比丘原本的戒師或道場中與他同修的十比丘裡,有任何一人不清淨,道場也就難成就。
若三七日後安住一百日,不起於座,有利根者能證須陀洹;就算尚未現前聖果,也可確信自己將來必成佛,不會有差錯。
這整個過程,就是我所教示的道場安立之法。
註解:
為什麼要供養十方如來及菩薩像?在壇室四壁供奉十方如來及菩薩像?所以說佛教教導有為法。
咒文
佛陀先解釋了楞嚴咒的無比威德力,能護法安國、破除災厄、讓行者不受外道魔事干擾。假如行者過去無量劫以來,尚有各種罪障,未及懺悔;只要能讀誦、書寫這咒、佩帶或安住在居處,這些長久積存的惡業,就像雪遇到熱水,迅速消解,乃至於悟無生忍。
註解:
有些咒文也許有用,但不可能像經文寫得那般神奇。
受報
佛陀對阿難說:「六報,眾生由六識(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)各自造下惡業,臨終時就從六根(見、聞、嗅、嘗、觸、思)引發對應的苦報。這些苦報大多在地獄,但並不僅限於此。眾生因前世、宿債,以及各種貪嗔癡等妄想,還可能受生鬼道、畜生道;或是憑某些偏巧之法入仙道;乃至生到欲界諸天。總歸都是迷妄所造,不是本來就有。」
楞嚴經列舉了各種受報,墜無間獄:成焦丸、鐵糜、諸毒虫周滿身體、為爛、為大肉山,有百千眼無量𠯗食、飛砂礰擊碎身體、燋爛骨髓、眾口亂噬、火狗、牛頭獄卒等惡相。
註解:
也許某些地獄的形象存在,但經文總是把它寫得很恐怖,好像一些問題就會下地獄、落鬼道、畜生道,永無出期,經過劫數烈火煉罪之後,罪報終了。這些只是威脅,對於修行並沒有什麼實質幫助。
嚴肅的說,各種地獄的恐怖景象,噁心的形象到底是誰想出來的?哪類人可以想出這麼多邪惡、噁心的東西?這反映了不堪的內在現實。
眾多佛經中各種人天鬼神都來集,如果不是真正能分清,這類連結很容易導致一個人的精神變得混亂不清,邏輯脫序。
經文講解各種地獄景象、各種鬼類、仙類,不同階位,幾重天,其真實性有待確鑿,況且對於見性解脫意義不大。
卷八
三漸次除妄想
「若要修成佛的三摩地,就得針對這原始亂想,分三步驟(三漸次)才能徹底去除。就像想用一只乾淨容器裝甘露,必先倒掉原本的毒蜜,再以湯水加灰香洗淨,之後才可盛放甘露。」
註解:
就像達摩和六祖說的,本具佛性,把蒙蔽的拆除了,就見到自性。不用佛教這麼麻煩的漸次修行,整個方向都帶錯了,越繞越遠。
《楞嚴經》的教導不是跳脫三界,反而困在三界中。【若飛心中兼福兼慧及與淨願,自然心開見十方佛,一切淨土隨願往生。】見性解脫是跳說三界,但經文卻反覆解釋三界內的事物,教人往生淨土,讓人困在幻中幻,夢中夢。
卷九
絞盡腦汁,暫時放棄。
卷十
暫時放棄,楞嚴經的繁冗太令人崩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