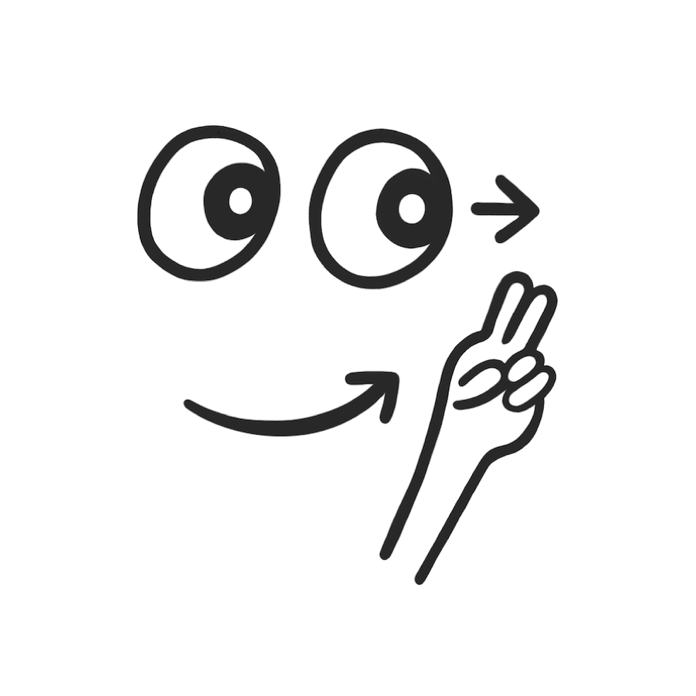解析《六祖壇經》
《六祖壇經》簡稱《壇經》。「六祖」因為惠能是禪宗第六祖。
雖然《壇經》基本上代表了惠能的思想,也代表了禪宗的思路。可以從其獨樹一格的思維風格見得,但壇經的內容問題其實很多。壇經從唐朝以來,歷代很多後人重新編排,重新詮釋,出現了很多版本,有些詮釋錯了,有些內容則是被增添上去的。也因為六祖惠能不識字,壇經並不是他自己寫的,而是他的弟子編輯而成,有些內容大概從一開始就詮釋錯誤了。
這篇解析只摘錄並探討《六祖壇經》的關鍵概念:
「本來無一物,何處惹塵埃?」
自性,即是佛性
「住心觀靜,是病非禪;長坐拘身,於理何益?」「道由心悟,豈在坐也?」
用而不住:「用即遍一切處,亦不著一切處。」
禪定
不著空:玩空、無記空、斷滅空
空性、性空:「世界虛空,含藏萬物色像⋯⋯須彌諸山,總在空中。世人性空,也是如此。」
「佛法在世間,不離世間覺。」
沒有頓漸,沒有次第:「自性自悟,頓悟頓修,亦無漸次,所以不立一切法。諸法寂滅,有何次第?」
無功德,達磨與梁武帝的對話
無頓漸,無次第
著文字,著概念,頭腦的假想
本來無一物,何處惹塵埃?
惠能,唐朝時期,南方人,生活艱辛貧乏,在市場賣柴火。一天聽到客人在唸誦《金剛經》,也想學習,於是安置了母親,打包行李,動身前往參拜禪宗五祖弘忍。
跋涉了三十多天,到了湖北省黃梅。五祖問惠能:「你是哪裡人?想要求什麼?」惠能回答:「弟子是嶺南新州的百姓,從遠方來禮敬大師,唯有求成佛,不求其他事物。」五祖說:「你是嶺南的南方人,又是未受教化的夷蠻之人,如何堪作佛?」惠能說:「人雖有南北的差別,但佛性沒有南北的差別;夷蠻之人與和尚雖然不同,但佛性有什麼差別?」
有一天,五祖開始尋找著承接衣鉢的接班人,透過弟子所寫的偈來驗證是否見性,挑選合適人選。神秀寫下:
【身是菩提樹,心如明鏡台。時時勤拂拭,勿使惹塵埃。】
註解:身如一棵充滿智慧的菩提樹,心如一面明亮的銅鏡。時時勤勞擦拭,不讓它沾染塵埃。意思是修行就像擦拭一面明鏡,時刻保持警覺,不斷精進修行,避免煩惱與妄念污染內心。這是北宗神秀的修行觀,主張漸修,認為修行需要不斷努力,逐步去除內心的無明與煩惱,才能達到覺悟。
惠能不識字,請人為他讀誦,聽畢,也請人替他題上一偈:
【菩提本無樹,明鏡亦非台。本來無一物,何處惹塵埃?】
註解:惠能則有另一個領悟。菩提(覺悟)並不是一棵樹,明鏡也不是安放在台座上的實體,不是一個具象的存在。沒有明鏡臺(自性)本來空無一物,又怎麼會受到塵埃的污染呢?煩惱與妄念其實是執著所產生的。雖然有大腦,有身體,有念頭,但沒有認定或框架,則沒有了鏡台,塵埃隨處飄盪,但無處可附著,何來的沾染?無執,則無煩惱可染。
註解:兩首偈的表面上差異微小,近乎雞蛋中挑骨頭,但實則天差地遠。兩者真正差異在於:前者,心如明鏡,勤勞地擦亮鏡子,留意每一個起心動念,時刻提醒自己回到當下、放鬆心情、面帶微笑、不要愁眉苦臉。雖然自覺自省,幻垢沒有除盡,但沒有打破自我框架,只是給自我框架除鏽拋光。辛勤地觀心無相,光明皎潔,一念不生,虛靈寂照,但本質上並沒有瓦解問題的根基,則依舊在框架內遊走。後者六祖惠能則是「本來無一物,何處惹塵埃?」本來就沒有鏡子。
自性,即是佛性
【凡夫不會,從日至夜受三歸戒。若言歸依佛,佛在何處?若不見佛,憑何所歸,言却成妄⋯⋯經文分明言自歸依佛,不言歸依他佛。自佛不歸,無所依處。】
白話:普通人不理解,於是從早到晚,他們都在接受三歸戒。如果說要歸依佛,那麼佛究竟在何處?如果佛無形無相,找不到佛,又該憑什麼來歸依?因此那只是虛妄之言⋯⋯經文中明確說的是:歸依自心的佛,而不是歸依其他外面的佛。若不是歸依自心的佛,那就無處可歸依了。
註解:自心是佛,佛不在外。自性,即是佛性。
【自悟自修自性功德,是真歸依。皮肉是色身,色身是舍宅,不言歸依也。但悟自性三身,即識自性佛。】
白話:靠自己覺悟、自己修行,獲得自性功德,才是真歸依。皮肉只是一個虛幻不實的色身肉體,肉體只是一個暫時的住處,不能作為歸依。只要覺悟自己的本性,就會識得自性中的佛性。
註解:自性是佛,所以向外求佛,猶如騎驢覓驢。如果說,皈依,只是找回自己的本來面目。
住心觀靜,是病非禪
【又有迷人,空心靜坐,百無所思,自稱為大。此一輩人,不可與語,為邪見故。】
白話:有一些迷茫未悟的人,誤以為只要靜坐,追求心中空無一物,什麼也不思索,自以為達到高深境界,得「大智慧」。這樣的人是無法說明白的,因為他們見解有誤,不明白真實義。
註解:空心靜坐只是枯坐。
【善知識!又有人教坐,看心觀靜,不動不起,從此置功。迷人不會,便執成顛。如此者眾,如是相教,故知大錯。】
白話:另外,有些人教人靜坐,雖然觀察自己的心,但追求保持在「寂靜不動」和「不起念頭」的狀態,誤以為這樣修行有作用。迷惑的人沒有真正理解的修行方法,執著於這種方式,反而變得顛倒錯誤。這樣的人很多,他們還用這種錯誤的方法教導別人,這是一種很大的錯誤。」
【生來坐不臥,死去臥不坐,一具臭骨頭,何為立功課?】
白話:
活著的時候整天打坐,不肯躺下休息;可是死了後,身體橫躺在那裡,再也坐不起來了。我們這具身體,不過是一副會腐爛的臭皮囊而已,那你又為什麼要執著於各種「功課」?
註解:
執著於各種「功課」,形式上的坐禪、特定姿勢打坐、打坐幾個小時、誦經多少十萬遍、苦修⋯⋯這些是有為法,沒有真正觀照本心、契入真實,真正的修行不是身體上的苦行或表面上的功課,只是操勞這副臭皮囊而已,離開了實修的根本。
【道由心悟,豈在坐也。】
薛簡問道:「京城的禪宗修行者都說:『要想真正悟道,必須坐禪修習禪定。如果不依靠禪定,就無法得到解脫。』不知大師所說的法門如何?」
慧能大師答道:「道是靠內心領悟的,怎麼會在於打坐呢?《維摩詰經》說:『若有人認為如來是坐著、是躺著的,這樣的理解是走入了邪道。』為什麼呢?因為如來本無來去,無生無滅,這才是真正清淨的禪法。萬法本性空寂,這才是真正的如來禪坐。最終的覺悟,並非透過某種具體的修證來獲得,何況是打坐呢?」
用而不住
【用即遍一切處,亦不著一切處。但淨本心,使六識出六門,於六塵中無染無雜,來去自由,通用無滯,即是般若三昧、自在解脫,名無念行。若百物不思,當令念絕,即是法縛,即名邊見。】
心的運用遍及一切地方,但又不執著於任何地方。只要本心清淨,六識通過六門感知外界,六識(眼耳鼻舌身意)在六塵(色聲香味觸法)中不被染著,自由來去,運行順暢無阻,這就是般若三昧、自在解脫,稱為「無念行」。但如果對一切事物都不思考,刻意讓念頭完全斷絕,反而成為法上的束縛,稱為「邊見」,也就是偏執的錯誤見解。
如果什麼都不想、不思考,試圖讓念頭完全斷絕,反而成為法上的束縛,稱為「邊見」,也就是偏執、錯誤的見解。
註解:「無念」不是沒有念頭、沒有想法,但不困在某一個想法,繞不出來。
【於諸境上,心不染,曰無念。於自念上,常離諸境,不於境上生心。若只百物不思,念盡除却,一念絕即死,別處受生,是為大錯。】
白話:面對一切境界,心不染著,叫作『無念』。在自己的念頭上,不住於一切外境,不被外境所擾而生煩惱。但如果只是不思不想,試圖把念頭全部斷除,一個念頭斷絕了,就等同死亡,投生他處,一個大錯誤。
禪定
【何名禪定?外離相為禪,內不亂為定。外若著相,內心即亂;外若離相,心即不亂。本性自淨自定,只為見境,思境即亂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,是真定也。】
白話:什麼是禪定?不執著於外境形象,叫做「禪」,內心穩定,叫做「定」。如果你執著於外在形象,內心就會變得混亂;如果不住這些形象,心就會平靜。本性是清淨、穩定的,只因為見外境而著相,於是心煩意亂。如果看見各種外境,但內心依然不亂,那才是真正的定。
【「惟論見性,不論『禪定』解脫。」宗問:「何不論禪定解脫?」惠能回答:「為是二法,不是佛法。佛法是不二之法。」】
白話:
六祖說:「我們只探討『見性』,不討論『禪定』和『解脫』。」
弟子問:『為什麼不討論禪定和解脫?』
惠能回答:『因為禪定和解脫是二法,是二元對立的概念,不是佛法。佛法是「不二之法」,是超越二元對立的。』
註解:
空性、性空
【何名摩訶?摩訶是大。心量廣大,猶如虛空,無有邊畔,亦無方圓大小,亦非青黃赤白,亦無上下長短,亦無瞋無喜,無是無非,無善無惡,無有頭尾。諸佛剎土,盡同虛空。世人妙性本空,無有一法可得。自性真空,亦復如是。】
白話:何謂「摩訶」?「摩訶」的意思是「大」。心量廣大,猶如虛空,沒有邊界,也無固定的形狀大小,沒有顏色,沒有高低長短,沒有喜怒哀樂,沒有是非對錯,也沒有善惡之分,沒有起點與終點。一切佛國淨土,如同虛空一般,廣無邊際。世人的本性原本也是這樣,無有一法可以執著。自性本空,亦是如此。
註解:這裡不是在說有容乃大,包容一切,而是在說自性的本質無邊無際,猶如虛空。
【世界虛空,能含萬物色像,日月星宿,山河大地,泉源谿澗,草木叢林,惡人善人,惡法善法,天堂地獄,一切大海,須彌諸山,總在空中。世人性空,亦復如是。】
白話:世界的本質是虛空的,卻含藏一切現象和事物。無論是日月星辰、山河大地、泉水溪流、草木森林、善人惡人、好事壞事、、天堂地獄、廣闊的海洋,甚至像須彌山這樣的高山,所有這些都含藏在這虛空中。
註解:
這裡說「世界虛空,能含萬物色像。」並不是說虛空有容乃大,有氣度,可以「包容」日月星辰、山河大地、善惡人法⋯⋯而是說自性、空性投射出了萬事萬物,一切都含藏在其中。「世人性空,亦復如是。」
【自性能含萬法是大,萬法在諸人性中。若見一切人、惡之與善,盡皆不取不捨,亦不染著,心如虛空,名之為大,故曰摩訶。】
自性能涵融萬事萬物,萬法都存在於每個人的本性之中。如果能夠看待一切人事物,善惡之事,都不執著、不排斥、不染著,心境如同虛空般廣大無邊,這就是「大」的真正含義,因此,稱之為 「摩訶」。
註解:
一些萬事萬物都是自性的投射。既然是自性的投射,就不能認定所謂的善,所謂的惡,否則會困在二元分裂的思維狀態中。但矛盾的是,這不代表你不知道什麼是善良,什麼叫邪惡,因為很明顯的,有些事情會帶給你快樂,例如關愛、同理,有些會帶給你痛苦,例如傷害他人。生理上會有喜歡的偏好,例如喜歡花的香味,不喜歡臭水溝的惡臭,生理上不可能不分別。
「知道」但不「認定」,也許某些行為傷害了別人,造成了別人的痛苦,但問題可以修正,錯誤可以悔改,但不把自己或他人定罪。雖然知道人性是佛家所說的「無明」。
【此法門中,坐禪元不著心,亦不著凈,亦不言動。若言看心,心元是妄。妄如幻故,無所看也。若言看凈,人性本凈。為妄念故,蓋覆真如⋯⋯看心看凈,卻是障道因緣。】
白話:
這法門的坐禪,不要執著自己的念頭,也不刻意追求所謂的清淨,更不用刻意保持心念不動。
如果說觀看這顆心,「心」本來就虛妄不實。妄心就像幻影一般,沒有真實形象,所以沒有真正可以「看」的。
如果說要觀看「清淨」,人的自性本來就是清淨的,只因為妄念的緣故,遮蔽了真如本性。只要沒有妄想,本性自然清淨。如果不了解自性本來清淨,卻刻意去追求所謂的清淨,反而會產生一種對『清淨』的執著,投射出一種「清淨」的妄念、想像。(註:猶如 UG 克里希納穆提,說的:「你認為的神聖莊嚴都在污染你的心智。」)
「清淨」本身無形無相,如果建立了一個「清淨」的形象,誤以為是修行功夫。這種見解反而會障蔽自己的本性,被想像出來的『清淨』的概念所束縛。
如果說「不動」,看見別人缺失過錯,而不去分別他們的過錯,則是自性不動。那些迷惑的人,自己說「不動」,卻一開口就批評別人的是非善惡,這樣其實與修道相違背的。
執著於看「心」,看「清淨」,都是阻礙你開悟的原因。
不著空:玩空、無記空、斷滅空
【莫聞吾說空,便即著空。第一莫著空,若空心靜坐,即著無記空。】
白話:不要聽我說『空』,就執著於『空』。最重要的是,不要執著於空相!如果空心靜坐,靜坐不起任何念頭,那是執著於『無記空』。
佛法在世間,不離世間覺
【佛法在世間,不離世間覺,離世覓菩提,恰如求兔角。】
佛法就在這世界之中,不離開世間才可能覺悟。如果離開世間去尋找菩提(覺悟),就像在找頭上長角的兔子。
【若欲修行,在家亦得,不由在寺。在家能行,如東方人心善;在寺不修,如西方人心惡。但心清淨,即是自性西方。】
白話:如果想要修行,無論是在家還是在寺廟,都可以。修行不一定非得在寺廟。在家的修行者,就像東方的人,心地善良;而在寺廟中若不修行,就像西方的人,心地惡劣。只要心中清淨,就能達到自性的西方境界。
無功德,達磨與梁武帝的對話
韋刺史為六祖大師舉辦了一場盛大的齋會。齋會結束後,韋刺史請大師登上法座,自己和官員、百姓一起恭敬地向大師禮拜,然後問道:「弟子聽和尚說法,實在覺得不可思議。現在有一些疑問,希望和尚大發慈悲,特別為我們解說。」
六祖說:「有疑問就問吧,我會為你們解說。」
韋刺史問:「和尚所說的法,是達摩大師的宗旨嗎?」
六祖回答:「是的。」
韋刺史說:「弟子聽說:達摩大師當初教化梁武帝時,武帝問:『我一生建造寺廟、剃度僧人、布施設齋,有什麼功德?』達摩大師回答:『實際上沒有功德。』弟子不明白這個道理,希望和尚為我們解說。」
六祖說:「確實沒有功德,不要懷疑聖人的話。梁武帝的心態不正,不明白真正的佛法。建造寺廟、剃度僧人、布施設齋,這些只是求福報,不能把福報當作功德。功德在法身中,不在修福報。」
六祖接著說:「見本性是「功」,平等心是「德」。心念不執著於外境,覺照本性,在日常生活中靈活運用,才是真正的「功德」。
註解:
「見性是功,平等是德。」「功德」這個詞由「功」與「德」兩個概念組成:「功」是內心修行的實踐;「德」是顯現出來的精神品質。「功」是「原因」;「德」是「結果」。
「念念無滯,常見本性」是結果,不是一種練習。所以「念念無間是功,心行平直是德。」不可能刻意念念相續不斷地保持正念,那是一個極為耗神的作用。但如果回到了自性,內心則不會因為某種認定而生起莫名執念,被自己的執念所煩擾、所困。疑後人解釋有誤。
「是以福德與功德別。」功德是內在的修行,從自性中自然體證,不是靠世間的有為法,布施、供養所求得,所以「福德」和「功德」是不同的。
念阿彌陀佛,就能轉生西方淨土?
【刺史又問曰:「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,願生西方。請和尚說,得生彼否?願為破疑。」
師言:「使君善聽,惠能與說。世尊在舍衛城中,說西方引化。經文分明,去此不遠。若論相說,里數有十萬八千,即身中十惡八邪,便是說遠。說遠為其下根,說近為其上智。人有兩種,法無兩般。迷悟有殊,見有遲疾。迷人念佛求生於彼,悟人自淨其心。所以佛言:『隨其心淨即佛土淨。』使君東方人,但心淨即無罪。雖西方人,心不淨亦有愆。東方人造罪,念佛求生西方。西方人造罪,念佛求生何國?凡愚不了自性,不識身中淨土,願東願西。悟人在處一般,所以佛言:『隨所住處恒安樂。』使君心地但無不善,西方去此不遙。若懷不善之心,念佛往生難到。】
白話:
刺史問道:「弟子常常見到僧人與在家信眾念阿彌陀佛,希望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請問大師,這樣真的能去嗎?請為我們解答疑惑。」
六祖惠能說:「請使君用心聆聽,我來為你解說。當年世尊在舍衛城講說《阿彌陀經》,引導眾生向往西方極樂世界。經典中提到,極樂世界離此地並不遙遠。如果從表面理解,以世間距離來看,的確有十萬八千里之遠。然而,這個數字其實象徵著人內心的『十惡八邪』,若內心充滿貪、瞋、癡等惡念,當然覺得極樂世界遙不可及。根器較鈍的人會說『遠』在天邊;但對於根器高的人,則『近』在眼前。
人有兩種,迷與悟,但法只有一種。迷悟有差別,見性過程有快慢。迷者向外求,希望念佛往生極樂世界;而悟者向內尋,明白真正的修行是清淨自己的內心。因此佛說:『自己的心清淨了,則佛土清淨。』(「佛土」 指的是佛國淨土,也可以理解為外在環境。)
假如你是東方人,只要內心清淨,就不會有罪惡;即使是西方人,若心不清淨,同樣會造罪。東方人造了罪,念佛求生西方;那麼西方人造了罪,又該求生何處呢?
愚癡之人不明白自己的本性,不懂身心之內的淨土,總是希望往東或往西尋找。而真正覺悟的人,在任何地方都能安住,正如佛說:『隨所住處,恆安樂。』如果使君內心沒有邪惡,那麼西方淨土離你並不遙遠;但若內心充滿不善,即使口中念佛也很難到。
註解:
念誦佛號,阿彌陀佛,就能到西方極樂世界?一個人的內在現實就是往生後去的地方,轉生到自己投射出來,想像出來的境界。
無頓漸,無次第
【善知識!本來正教,無有頓漸,人性自有利鈍。迷人漸修,悟人頓契。自識本心,自見本性,即無差別,所以立頓漸之假名。】
白話:教法本來沒有頓悟和漸修的區別,只是人的根性有敏捷和遲鈍的不同。迷惑的人需要漸修,有領悟力的人可以當下覺悟並與真理契合。如果能認識自己的本心,見到本性,就沒有頓漸的差別,所以頓漸只是假名。
著文字,著概念,頭腦的假想
有一個童子,名叫神會,是襄陽高家的孩子,年僅十三歲,從玉泉寺來參拜惠能大師。惠能大師問他:「善知識遠道而來,辛苦了。你還帶來了你的本來面目嗎?如果有本來面目,就應該認識主人。你試著說說看。」
神會回答:「以無住為本,見性就是主人。」
惠能大師說:「你這小沙彌怎麼輕率地說這種言論?」
神會反問:「和尚坐禪時,還見不見?」
惠能大師用拄杖打了神會三下,問:「我打你,你痛不痛?」
神會回答:「也痛也不痛。」
惠能大師說:「我也見也不見。」
神會問:「什麼是『也見也不見』?」
惠能大師說:「我所見的,是常常反省自己,不見他人的是非好惡,所以說是『也見,也不見』。你說『也痛,也不痛』是什麼意思?如果你不痛,就和木石一樣;如果你痛,就和凡夫一樣,會生起怨恨。你剛才問的『見、不見』是二元分別,但『痛、不痛』是生滅的分別。你連自己的自性都沒見到,還敢來戲弄人!」
神會聽了,禮拜懺悔。惠能大師又說:「如果你心裡迷惑,不見自性,就該去請教善知識,尋找道路。如果你心裡覺悟,就應該自己見性,依法修行。你自己迷失不見自性,卻來問我見不見。我的見性我自己知道,難道能代替你解開迷惑嗎?如果你自己見性,也不能代替我解開迷惑。為什麼不自己覺悟、自己見性,卻來問我見不見呢?」
註解:
惠能批評神會,認為他的回答雖然看似有道理,但缺乏真正的體悟,只是停留在表面的理論層次,沒有真正見性。修行不在於口頭上的機鋒問答,而是內心的真實覺悟。
痛與不痛,這類似是而非的邏輯類似黃檗的「終日吃飯,未曾咬著一粒米;終日行,未曾踏著一片地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