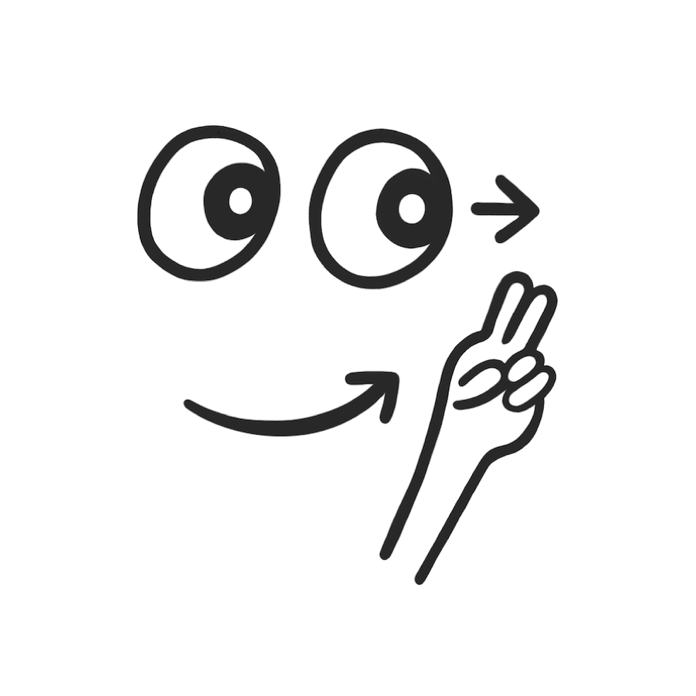《我可能錯了?》一個錯誤的假設,害慘了一位誠心求道者
《我可能錯了:森林智者的最後一堂人生課》是一本由瑞典作者Lindeblad撰寫的心靈暢銷書。
Lindeblad年輕時曾在跨國企業任職,擁有體面的收入、配車與秘書,外表看似風光卻內心空虛。他在心靈上尋找不到意義,日積月累逐漸產生不安、恐懼與焦慮,強烈渴望突破這種困境。
某天,他腦中浮現一句「是該往前走的時候了」,於是他在26歲時毅然辭職,踏上自我探索之路。一次旅遊中,Lindeblad因感情受創,帶著痛苦的心情意外接觸佛法,試圖透過出家修行尋找內心的寧靜與「回家的感覺」。
在泰國的傳統佛教僧團的規範中,常見的「每日一食、過午不食」,以及對物質的極度壓縮,使他在修行過程裡遇到種種身心衝擊。例如:僅能在中午化緣得食,所有食物攪拌在大桶裡再分食,且不時夾雜雞毛、魚乾等令人難以下嚥的元素。
長期下來,他內心對食物的渴望反而加劇,一旦想到心愛的甜點,或是看到隔壁屋冰箱裡的冰啤酒,就會焦躁不安。種種「苦行」看似在修煉耐力,卻也帶來另一種執著與心理煎熬。
強制性的「壓縮食物」和「苦行」,並不見得能帶來真正的覺悟。泰國部分寺院中,甚至因僧侶下午飢餓而大量攝取含糖飲料,導致肥胖、糖尿病等病症比例提升。
從生理角度來看,每日一食可能傷身,過度逼迫自己熬夜冥想或以縫衣針刺手、用布條吊頭避免倒下,其實只是一種為了「保持警覺」的苦行模式,未必真正達到「清醒」。
此外,傳統的修行規範,例如禁碰金錢、不能選擇何時何地與何物進食、不得挑選室友與住宿地點等,雖然的確練習了「放棄控制」,卻也可能造成對現實生活的無能為力。Lindeblad曾與同伴站在渡輪碼頭兩小時,只為等待好心人買票,因為僧侶不能碰錢。這種「無」,對他而言,如同切斷了慾望與控制,也切斷了更多自由。
他曾認為「無」就是幸福,認為應該拋下一切、無慾無求才能解脫。但幻相中的『無』不是真實的存有,真實世界仍有痛覺、情緒與想法,若壓抑和關閉所有感受,只是把自己『沉到水裡』,反而是一種無奈、痛苦的過程。要丟掉的並非金錢與物質,而是錯亂或狹隘的想法。苦行若無法真正消除內心渴望,只會讓人困在「瑪雅的陷阱」中。
另一方面,泰國寺院住持常鼓勵一句話:「我可能錯了。」當人即將和他人起衝突時,若能重複三次「我可能錯了」,或許能放下執著與擔憂,用開放的心態接納更多可能。這句話確實富有省思的力量,但也可能帶來另一層疑惑:若一個人自信心不足,或不知該如何邁下一步,將所有念頭都歸咎為「我錯了」,最終容易陷入全面的自我懷疑與自我否定。
對Lindeblad來說,幼時那種「我不夠好」「害怕被揭穿」的想法,是文化與家庭背景遺傳下的心靈枷鎖,也使得「我可能錯了」成為他安撫矛盾與痛苦的方式。然而,痛苦的根源既可能來自自我認定,也可能源於外界限制;如何真正看清並化解,是更深的課題。
在佛寺修行17年,他最大的體悟是:「我對自己的念頭再也不全然相信了,這是我的超能力。」他認為痛苦是念頭所生,但念頭本身也能帶來創造力與解決問題的可能,無法一概否定。關鍵或許在於探究「哪種念頭引發痛苦」,了解內心在糾結什麼,才能真正解決問題。如果只用「不要相信念頭」來壓制,可能只是暫時把念頭推開,問題依然存在。
最終,Lindeblad在聲音的指引下選擇還俗。回到瑞典後,卻因長期脫離社會而面臨種種不適應,陷入憂鬱,再者罹患了漸凍症(ALS)。他在病中寫下本書,告白了對身體的感謝,也承諾當身體無法再支撐時,會尊重身體的意願。書中可感受到他反覆將「我可能錯了」這句話吞下,又在生命關頭吐露對真實自我的渴望——那份「回家」的感覺,是他八歲時短暫體驗的內心寧靜,一直是他一生所尋覓的歸宿。
然而,17年的苦修並未完全帶他「回家」,僧團的生活模式反而讓他倍感壓抑。當他終於決定鬆開這一切,卻又迎來生理病痛的挑戰,憂鬱與身體衰退交織成一種悲涼。
我們之所以分享這本書,是因為對Lindeblad的「冤望路」感同身受:一個真誠求道者,用盡全力想回到那份童年時刻的寧靜,卻在各種規範中消磨了大半生。或許,也正因這樣的試煉,他才在最終體悟到「回家」並非否定自我或壓制情緒,而是在那些深藏的痛苦裡、在命運的安排下,慢慢學習與自我和解。
最終,他將這些經歷匯聚於《我可能錯了》一書,既是對自己的一次真誠告白,也讓更多人在翻閱時,獲得反思與安慰。